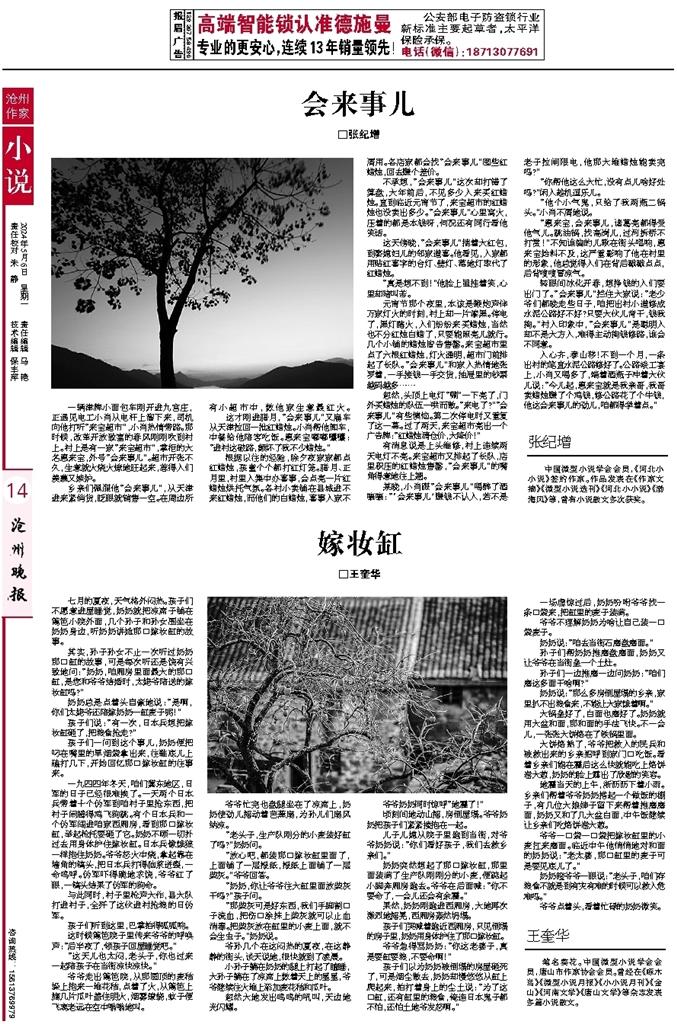□王奎华
七月的夏夜,天气格外闷热。孩子们不愿意进屋睡觉,奶奶就把凉席子铺在篱笆小院外面,几个孙子和孙女围坐在奶奶身边,听奶奶讲她那口嫁妆缸的故事。
其实,孙子孙女不止一次听过奶奶那口缸的故事,可是每次听还是饶有兴致地问:“奶奶,咱厢房里面最大的那口缸,是您和爷爷结婚时,太姥爷陪送的嫁妆缸吗?”
奶奶总是点着头自豪地说:“是啊,你们太姥爷还陪嫁奶奶一缸麦子呢!”
孩子们说:“有一次,日本兵想把嫁妆缸砸了,把粮食抢走?”
孩子们一问到这个事儿,奶奶便把叼在嘴里的旱烟袋拿出来,往鞋底儿上磕打几下,开始回忆那口嫁妆缸的往事来。
一九四四年冬天,咱们冀东地区,日军的日子已经很难挨了。一天两个日本兵带着十个伪军到咱村子里抢东西,把村子闹腾得鸡飞狗跳。有个日本兵和一个伪军闯进咱家西厢房,看到那口嫁妆缸,举起枪托要砸了它。奶奶不顾一切扑过去用身体护住嫁妆缸。日本兵像饿狼一样抱住奶奶。爷爷怒火中烧,拿起靠在墙角的镐头,把日本兵打得脑浆迸裂,一命呜呼。伪军吓得跪地求饶,爷爷红了眼,一镐头结果了伪军的狗命。
与此同时,村子里枪声大作,县大队打进村子,全歼了这伙进村抢粮的日伪军。
孩子们听到这里,巴掌拍得呱呱响。
这时候篱笆院子里传来爷爷的呼唤声:“后半夜了,领孩子回屋睡觉吧。”
“这天儿也太闷,老头子,你也过来一起陪孩子在当街凉快凉快。”
爷爷走出篱笆院,从那圆顶的麦秸垛上抱来一堆花秸,点着了火,从篱笆上摘几片瓜叶盖住明火,烟雾缭绕,蚊子便飞离老远在空中嗡嗡地叫。
爷爷忙完也盘腿坐在了凉席上,奶奶使劲儿摇动着芭蕉扇,为孙儿们扇风纳凉。
“老头子,生产队刚分的小麦装好缸了吗?”奶奶问。
“放心吧,都装那口嫁妆缸里面了,上面铺了一层报纸,报纸上面铺了一层柴灰。”爷爷回答。
“奶奶,你让爷爷往大缸里面放柴灰干吗?”孩子问。
“那柴灰可是好东西,我们手脚割口子流血,把伤口涂抹上柴灰就可以止血消毒。把柴灰放在缸里的小麦上面,就不会生虫子。”奶奶说。
爷孙几个在这闷热的夏夜,在这静静的街头,谈天说地,很快就到了凌晨。
小孙子躺在奶奶的腿上打起了瞌睡,大孙子躺在了凉席上数着天上的星星,爷爷继续往火堆上添加麦花秸和瓜叶。
忽然大地发出呜呜的吼叫,天边地光闪耀。
爷爷奶奶同时惊呼“地震了!”
顷刻间地动山摇,房倒屋塌。爷爷奶奶把孩子们紧紧搂抱在一起。
儿子儿媳从院子里跑到当街,对爷爷奶奶说:“你们看好孩子,我们去救乡亲们。”
奶奶突然想起了那口嫁妆缸,那里面装满了生产队刚刚分的小麦,便踮起小脚奔厢房跑去。爷爷在后面喊:“你不要命了,一会儿还会有余震。”
果然,奶奶刚跑进西厢房,大地再次激烈地摇晃,西厢房轰然坍塌。
孩子们哭喊着跑近西厢房,只见倒塌的房子里,奶奶用身体护住了那口嫁妆缸。
爷爷急得骂奶奶:“你这老婆子,真是要缸要粮,不要命啊!”
孩子们以为奶奶被倒塌的房屋砸死了,可是烟尘散去,奶奶却慢悠悠从缸上爬起来,拍打着身上的尘土说:“为了这口缸,还有缸里的粮食,俺连日本鬼子都不怕,还怕土地爷发怒啊。”
一场虚惊过后,奶奶吩咐爷爷找一条口袋来,把缸里的麦子装满。
爷爷不理解奶奶为啥让自己装一口袋麦子。
奶奶说:“咱去当街石磨盘磨面。”
孙子们帮奶奶推磨盘磨面,奶奶又让爷爷在当街垒一个土灶。
孙子们一边推磨一边问奶奶:“咱们磨这多面干啥啊?”
奶奶说:“那么多房倒屋塌的乡亲,家里扒不出粮食来,不能让大家饿着啊。”
大锅垒好了,白面也磨好了。奶奶就用大盆和面,那和面的手法飞快。不一会儿,一张张大饼烙在了铁锅里面。
大饼烙熟了,爷爷把救人的民兵和被救出来的乡亲招呼到家门口吃饭。看着乡亲们能在震后这么快就能吃上烙饼卷大葱,奶奶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地震当天的上午,淅沥沥下着小雨。乡亲们帮着爷爷奶奶搭起一个做饭的棚子,有几位大娘婶子留下来帮着推磨磨面,奶奶又和了几大盆白面,中午饭继续让乡亲们吃烙饼卷大葱。
爷爷一口袋一口袋把嫁妆缸里的小麦扛来磨面。临近中午他悄悄地对和面的奶奶说:“老太婆,那口缸里的麦子可是要见底儿了。”
奶奶瞪爷爷一眼说:“老头子,咱们存粮食不就是到有灾有难的时候可以救人危难吗。”
爷爷点着头,看着忙碌的奶奶微笑。
王奎华
笔名葵花。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员,唐山市作家协会会员。曾经在《啄木鸟》《微型小说月报》《小小说月刊》《金山》《河南文学》《唐山文学》等杂志发表多篇小说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