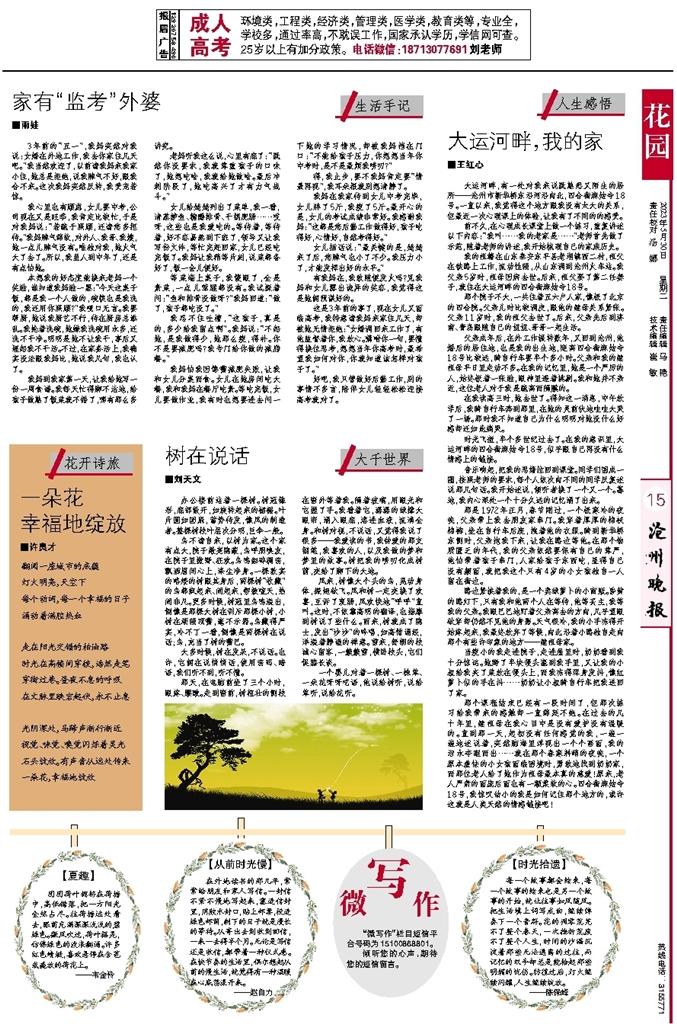大运河畔,有一处对我来说既熟悉又陌生的居所——沧州市新华桥东沿河沿向北,四合街麻姑寺18号。一直以来,我觉得这个地方跟我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最近一次心理课上的体验,让我有了不同的的感受。
前不久,在心理成长课堂上做一个练习,重复讲述以下内容:“我叫……我的老家是……”老师首先做了示范,随着老师的讲述,我开始梳理自己的家族历史。
我的祖籍在山东泰安东平县老湖镇西二村,祖父在铁路上工作,流动性强,从山东调到沧州火车站。我父亲5岁时,祖母因病去世。后来,祖父娶了第二任妻子,就住在大运河畔的四合街麻姑寺18号。
那个院子不大,一共住着五六户人家,像极了北京的四合院。父亲儿时比较调皮,跟他的继母关系紧张。父亲11岁时,我的祖父去世了。后来,父亲先后到济南、青岛跟随自己的姐姐、哥哥一起生活。
父亲成年后,在外工作辗转数年,又回到沧州,他婚后的居住地,也是我的出生地,距离四合街麻姑寺18号比较远,骑自行车要半个多小时。父亲和我的继祖母平日里走动不多。在我的记忆里,她是一个严厉的人,始终板着一张脸,眼神里透着挑剔。我和她并不亲近,这位老人对于我是疏离而隔膜的。
在我读高三时,她去世了。得知这一消息,中午放学后,我骑自行车奔到那里,在她的灵前伏地哇哇大哭了一场。那时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明明对她没什么好感却还如此痛哭。
时光飞逝,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在我的意识里,大运河畔的四合街麻姑寺18号,似乎跟自己再没有什么情感上的链接。
音乐响起,把我的思绪拉回到课堂。同学们围成一圈,按照老师的要求,每个人依次向不同的同学反复述说那几句话。我开始述说,倾听者换了一个又一个。蓦地,我内心深处一个十分久远的记忆涌了出来。
那是1972年正月,春节刚过,一个极寒冷的夜晚,父亲带上我去朋友家串门。我穿着厚厚的棉袄棉裤,坐在自行车后座,拽着他的衣服。骑到新华桥东侧时,父亲抱我下来,让我在路边等他。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我的父亲依然要保有自己的尊严,他怕带着孩子串门,人家给孩子东西吃,显得自己没有颜面,就把我这个只有4岁的小女孩独自一人留在街边。
路边紧挨着我的,是一个卖绿萝卜的小商贩。昏黄的路灯下,只有我和他两个人在等待,他等买主,我等我的父亲。我眼巴巴地盯着父亲离去的方向,几乎望眼欲穿却仍然不见他的身影。天气很冷,我的小手冻得开始疼起来,我最终放弃了等候,向北沿着小路独自走向那个有些许印象的地方——继祖母家。
当瘦小的我走进院子,走进屋里时,奶奶看到我十分惊诧。她掰了半块馒头塞到我手里,又让我的小叔给我夹了菜放在馒头上,而我冻得浑身发抖,像红萝卜似的手在抖……奶奶让小叔骑自行车把我送回了家。
那个课程结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那次练习给我带来的感触却一直绵延不绝。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继祖母在我心目中是没有爱护没有温暖的。直到那一天,起初没有任何感觉的我,一遍一遍地述说着,突然脑海里浮现出一个个画面,我的泪水夺眶而出……就在那个春寒料峭的夜晚,一个原本羞怯的小女孩面临困境时,勇敢地找到奶奶家,而那位老人给了她作为祖母最本真的慈爱!原来,老人严肃的面庞后面也有一颗柔软的心。四合街麻姑寺18号,我惊叹幼小的我是如何记住那个地方的,或许这就是人类天然的情感链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