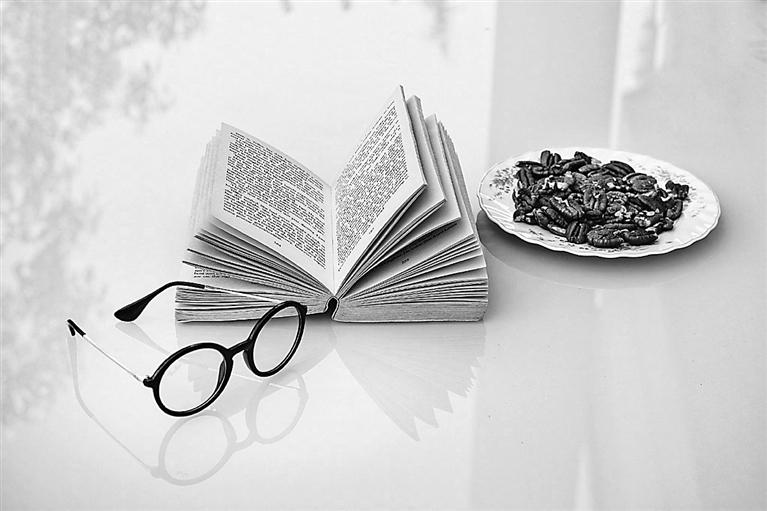汪曾祺说:“你很辛苦,很累了,那么坐下来歇一会儿,喝一杯不凉不烫的清茶,读一点我的作品。”
近日,读到汪老的散文集,他用平淡质朴的一支笔,写尽了草木之情,生活五味,世相百态。
他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他像一位和蔼慈祥的老人,用他饱经风霜的一生,告诉我们人生必须具备的三种能力。
慢,是人生的过程
小时候,听过一个故事。
印第安人赶着羊群朝着日落的地方走去,一开始他们行走的速度很快。
但是,每走过一段距离,他们都要停下来,等一等。
有一个过路人,很是好奇,就问印第安人,这是为什么?
印第安人平静地回答:“我们慢下来,是因为在等我们的灵魂赶上来。”
是的,慢,不是偷懒,而是为了等一等灵魂的步伐,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汪老在《葡萄月令》一文中,对葡萄的出窖、上架、浇水、喷药、打梢、掐须、膨大、着色、成熟、下架、入窖,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和描写。
一月,下大雪。雪静静地下着。葡萄睡在铺着白雪的窖里。
二月里刮春风。雪化了,土地是黑的……
八月葡萄着色,九月葡萄丰收……十二月葡萄入窖。
汪老用“慢”的视角和清澈、饱满的文字,从一月的葡萄睡在窖里写到十二月的葡萄完成了使命后,再次入窖,慢慢地品味,慢慢地观察,向读者展示了不同时节里葡萄的生长变化。
草木的成长是慢的过程,生活中的五味,也需要慢慢地品、慢慢地煨,才能感悟。
慢,不是懈怠
慢,是一步一个脚印,稳稳当当,到达目的地,以成熟的资态,屹立于世。
静,是人生的底色。一个人最核心的能力,是平静内心的能力。
空城计里,诸葛孔明把“平静”两字发挥到了极致。
他大开城门,而城内并无士兵迎战。
他镇定自若地在城楼上弹琴唱曲,波澜不惊。
正是这份平静,吓退了司马懿来势汹汹的追兵。
静下来,才能从容面对世间的纷繁喧闹;静下来,才能看云卷云舒,花开花落。
静,是什么?是物我两忘的境界,是看淡人世喧闹的理智和清醒。
读到汪老的《无事此静坐》,对“静”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和认识。
外祖父待客的几间空房,是难得的静室。
童年的汪老,是这里的常客,常常拿着一本书,悄悄走进去看书。童年养成的静坐习惯,让他一生受益。
1958年夏,汪老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他被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和三十几个农业工人挤在一屋同住。
他在文中写道:“他们吵吵闹闹,打着马锣唱山西梆子,我能做到心如止水,照样看书、写文章。我有两篇小说,就是在震耳的马锣声中写成的。”
直到多年后,汪老还保持着静坐的习惯。每天安静地坐在沙发上,任思绪飞扬,任往事尽现眼底,想着想着,就写出了好文章。
熬,是人生必经之路
很多人都知道励志的竹子定律。
前4年,竹子仅仅长了3厘米。而从第5年开始,竹子以每天30厘米的速度快速成长,只用了短短6周,就长到了15米的高度。
竹子定律告诉我们,人生不仅需要储备,更需要熬,熬过那3厘米,才能出人头地。
汪老在《豆汁儿》中,有一段文字这样描述:熬豆汁只能用小火,火大了,豆汁儿一翻大泡,就“澥”了。
竹子需要熬,豆汁需要熬,生活需要熬。
人生的字典里,从来就没有“容易”两字。那段极其艰难的岁月里,有多少人没熬过人生的3厘米。
在被划为“右派”后,汪老所从事的劳动以西山种树的活最是繁重。
每天工作量极大,供应的吃食却不能果腹。每天只有两个馒头,一块大腌萝卜。
时值秋天,他就地取材,吃山上的酸枣,烧地里的蝈蝈。他就着馒头,边咬腌萝卜,边嚼烧蝈蝈,还对自己说:“这味道真是香。”
面对生活抛来的考验,汪老没有自怨自艾、呼天抢地,而是以豁达乐观的心态坦然面对。
他利用别人说闲话、唱戏的时间,拿起手中的笔,一日又一日地坚持写下去。
不为境遇所困,不为繁事所扰,纷嚷喧闹中,守住初心。
汪老熬过了人生最艰难的3厘米,守得云开见月明。
梁文道曾评价他说:“就像一碗白粥,熬得刚刚好。”
熬,不是对命运的妥协,而是沉淀自己、升华自已,最终活成最好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