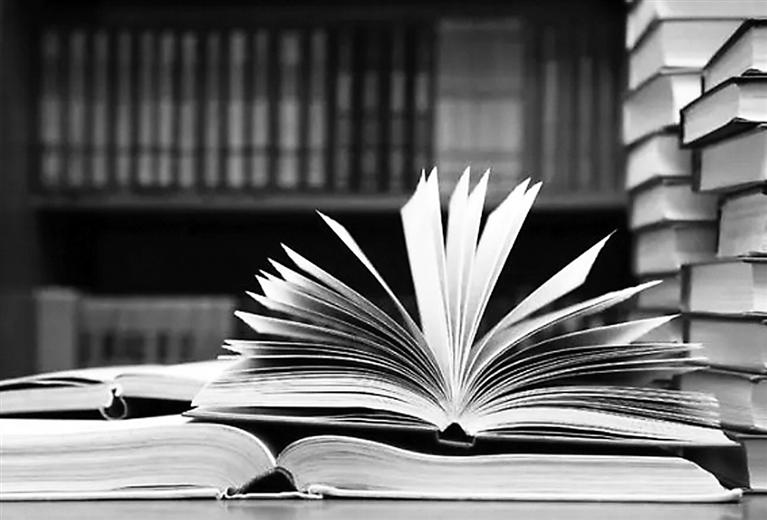“火车站里有火车,车站里边有旅客,旅客们,不是上车就是下车……”“好,再来一段!”喝彩声、鼓掌声、欢笑声,在深秋的乡村场院上响成一片。这,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乡村说书的场景。
在华北平原,乡村说书要选在地净场光的季节。这段日子,是乡亲们过得最舒坦的时光。秋庄稼收完了,小麦种上了,天气又不是太冷。于是,村里几位长辈便在街上喊住队长:“老三(队长在家里行三),请个说书的吧!”
老三应着,拎个布口袋,去仓库里装半袋玉米,背到四婶子家说:“说书的要来了,吃住就在你家。”
一村说书家家忙。说书的要来,各家各户都忙着请亲戚。傍晚,200瓦的电灯泡将场院照得亮如白昼。老人们早早坐在前排,叼着烟袋指指点点;年轻的小伙子们,拿着手电筒吆五喝六;小女孩们都是结伴而来,甩着辫子在人群里走来走去;女人们把锅碗收拾利索了,悄没声地坐在后边;而“熊孩子”们则爬墙上树,连喊带闹……这场景喧嚣而层次分明,如同画一样,镌刻在我的脑海里。
说书人一上来大多是先说个小段。比方,当年自行车还是个稀罕物,他就拿骑自行车的“开涮”:“两个轱辘一架梁,上面驮着个武大郎,见到老爷不下车,一个劲地摇铃铛……”接下来便是整本的大段,《三国》《水浒》,有时候也说《平原作战》《林海雪原》。他自己会设计许多“扣子”:“正在二人接头之际,忽听有人跑上楼来,欲知后事如何,明天接着说!”第二天,不由得你不早早去听。
热闹十天半个月后,四婶子去找队长:“说书的那些粮食快吃完了啊!”队长叹口气,从怀里掏出几块零钱说:“送说书先生走吧,明年咱们再请。”
如今,各类文化娱乐活动令人应接不暇,但乡村说书的情景总会在我的脑海中闪现。是说书人那鼓琴声,把关于文学的人生梦想植入了一个少年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