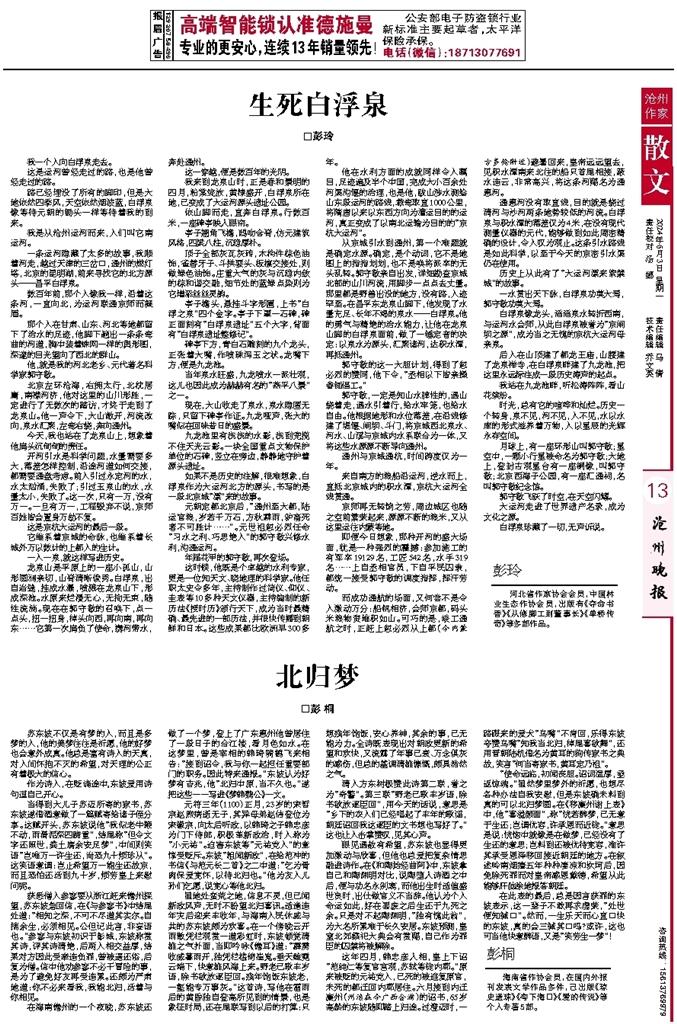我一个人向白浮泉走去。
这是运河曾经走过的路,也是他曾经走过的路。
路已经埋没了所有的脚印,但是大地依然四季风,天空依然烟波蓝,白浮泉像等待元朝的锄头一样等待着我的到来。
我是从沧州运河而来,人们叫它南运河。
一条运河隐藏了太多的故事,我顺着河走,越过天津的三岔口,通州的燃灯塔,北京的昆明湖,前来寻找它的北方源头——昌平白浮泉。
数百年前,那个人像我一样,沿着这条河,一直向北,为运河联通京师而凝眉。
那个人在甘肃、山东、河北等地都留下了治水的足迹,他脚下趟出一条条弯曲的河道,胸中装着蛛网一样的舆形图,深邃的目光望向了西北的群山。
他,就是我的河北老乡、元代著名科学家郭守敬。
北京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他对这里的山川形胜,一定进行了无数次的踏访,才终于走到了龙泉山。他一声令下,大山敞开,河流改向,泉水汇聚,左弯右绕,奔向通州。
今天,我也站在了龙泉山上,想象着他肩头沉甸甸的责任。
开河引水是科学问题,水量需要多大,落差怎样控制,沿途河道如何交接,都需要通盘考虑。前人引过永定河的水,水太汹涌,失败了;引过玉泉山的水,水量太小,失败了。这一次,只有一万,没有万一。一旦有万一,工程毁弃不说,京师百姓皆会置身万劫不复。
这是京杭大运河的最后一段。
它维系着京城的命脉,也维系着长城外万以数计的上都人的生计。
一人一泉,就这样写进历史。
龙泉山是平原上的一座小孤山,山形圆润亲切,山脊清晰俊秀。白浮泉,出自岩缝,挂成水瀑,喷溅在龙泉山下,形成深池。水原来烂漫无心,无拘无束,随性流淌。现在在郭守敬的召唤下,点一点头,扭一扭身,掉头向西,再向南,再向东……它第一次肩负了使命,携河带水,奔赴通州。
这一穿越,便是数百年的光阴。
我来到龙泉山时,正是春和景明的四月,粉棠绽放,黄棣盛开,白浮泉所在地,已变成了大运河源头遗址公园。
依山脚而走,直奔白浮泉。行数百米,一座碑亭映入眼帘。
亭子翘角飞檐,鸱吻含脊,仿元建筑风格,四梁八柱,沉稳厚朴。
顶子全部灰瓦灰砖,木构件棕色油饰,雀替牙子、斗拱耍头、板檩交接处,则做绿色油饰。庄重大气的灰与沉稳内敛的棕和谐交融,细节处的蓝绿点染则为它增添丝丝灵韵。
亭子檐头,悬挂斗字形匾,上书“白浮之泉”四个金字。亭子下罩一石碑,碑正面刻有“白浮泉遗址”五个大字,背面有“白浮泉遗址整修记”。
碑亭下方,青白石雕刻的九个龙头,正张着大嘴,作喷珠泻玉之状。龙嘴下方,便是九龙池。
当年泉水旺盛,九龙喷水一派壮观,这儿也因此成为赫赫有名的“燕平八景”之一。
现在,大山收走了泉水,泉水隐匿无踪,只留下碑亭作证。九龙哑声,张大的嘴似在回味昔日的盛景。
九龙池里有浅浅的水影,浅到兜揽不住天光云影。一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竖立在旁边,静静地守护着源头遗址。
如果不是历史的注解,很难想象,白浮泉作为大运河北方的源头,书写的是一段北京城“漂”来的故事。
元朝定都北京后,“通州至大都,陆运官粮,岁若千万石,方秋霖雨,驴畜死者不可胜计……”。元世祖忽必烈任命“习水之利、巧思绝人”的郭守敬兴修水利,沟通运河。
年届花甲的郭守敬,再次登场。
这时候,他既是个卓越的水利专家,更是一位知天文、晓地理的科学家。他任职太史令多年,主持制作过简仪、仰仪、圭表等10多种天文仪器,主持编制的新历法《授时历》颁行天下,成为当时最精确、最先进的一部历法,并很快传播到朝鲜和日本。这些成果都比欧洲早300多年。
他在水利方面的成就同样令人瞩目,足迹遍及半个中国,完成大小百余处河渠沟偃的治理,也是他,跋山涉水测绘山东段运河的路线,裁弯取直1000公里,将隋唐以来以东西方向为漕运目的的运河,真正变成了以南北运输为目的的“京杭大运河”。
从京城引水到通州,第一个难题就是确定水源。确定,是个动词,它不是地图上的指指划划,也不是唤将派卒的无头乱转。郭守敬亲自出发,详细勘查京城北部的山川河流,用脚步一点点去丈量。那里都是野兽出没的地方,没有路,人迹罕至。在昌平东龙泉山脚下,他发现了水量充足、长年不竭的泉水——白浮泉。他的勇气与精绝的治水能力,让他在龙泉山脚的白浮泉面前,做了一锤定音的决定:以泉水为源头,汇聚诸河,达积水潭,再抵通州。
郭守敬的这一大胆计划,得到了忽必烈的赞同,他下令,“丞相以下皆亲操畚锸倡工。”
郭守敬,一定是知山水脾性的,遇山绕着走,遇水引着行,给水牢笼,也给水自由。他根据地形和水位落差,在沿线修建了堤偃、闸坝、斗门,将京城西北泉水、河水、山溪与京城内水系联合为一体,又将这些水源源不断导向通州。
通州与京城通杭,时间跨度仅为一年。
来自南方的粮船沿运河,逆水而上,直抵北京城内的积水潭,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
京师再无转饷之劳,周边城区也随之空前繁荣起来,源源不断的粮米,又从这里运往内蒙等地。
即便今日想象,那种开河的盛大场面,犹是一种强烈的震撼:参加施工的有军卒19129名,工匠542名,水手319名……上自丞相官员,下自平民囚隶,都统一接受郭守敬的调度指挥,挥汗劳动。
而成功通航的场面,又何尝不是令人激动万分:船帆相济,会师京都,码头米粮物资堆积如山。可巧的是,竣工通航之时,正赶上忽必烈从上都(今内蒙古多伦附近)避暑回来,皇帝远远望去,见积水潭南来北往的船只首尾相接,蔽水连云,非常高兴,将这条河赐名为通惠河。
通惠河没有取直线,目的就是绕过清河与沙河两条地势较低的河流。白浮泉与积水潭的落差仅为4米,在没有现代测量仪器的元代,能够做到如此周密精确的设计,令人叹为观止。这条引水路线是如此科学,以至于今天的京密引水渠仍在使用。
历史上从此有了“大运河漂来紫禁城”的故事。
一水贯出天下脉,白浮泉功莫大焉,郭守敬功莫大焉。
白浮泉像龙头,滔滔泉水转折西南,与运河水会师,从此白浮泉被誉为“京闸坝之源”,成为当之无愧的京杭大运河母亲泉。
后人在山顶建了都龙王庙,山腰建了龙泉禅寺,在白浮泉畔建了九龙池,把这里永远标注成一段历史涛声的起点。
我站在九龙池畔,听松涛阵阵,看山花缤纷。
时光,总有它的喧哗和灿烂。历史一个转身,泉不见,河不见,人不见,水以水库的形式滋养着万物,人以星辰的光辉永存空间。
月球上,有一座环形山叫郭守敬;星空中,一颗小行星被命名为郭守敬;大地上,登封古观星台有一座铜像,叫郭守敬;北京西海子公园,有一座汇通祠,名叫郭守敬纪念馆。
郭守敬飞跃了时空,在天空闪耀。
大运河走进了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文化之源。
白浮泉珍藏了一切,无声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