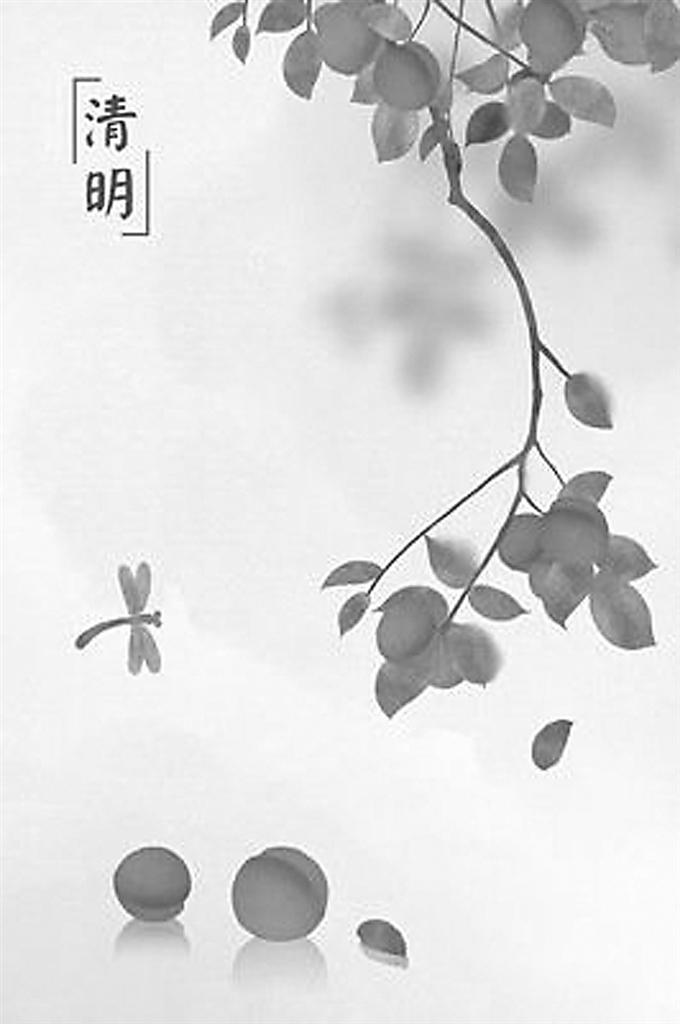郛堤城,一片枯黄的色调,朔风里萧瑟苍凉,那还是上世纪末初冬的场景。经过这座渤海湾边著名的古城时,我常会下车走进城内,登上五六米高的土墙,在那不宽的城墙顶上走上一段。人和羊踏出的小路略有弯曲地延伸到城墙的缺口,两旁干枯的马绊和各色野草紧紧地抓住墙土,挂着枯叶和干果的酸枣枝条横逸,枣刺尖利摆出一副威吓的姿态。放眼望去,城内那有低洼有小沟堰的土地上,有着残留的玉米秸秆,大片的芦花高高低低如浮动的雪原。
城墙根处,灰青的瓦砾和陶片或裸露或半掩在土,荒草试图用柔弱的身姿遮掩这些二千年前的遗存。俯身拾起一块不规则的凹形陶片,抚摸着绳纹的纹楞,有与当初古人同样轻抚时的感觉,将这粗糙的陶片轻掷于草下,它是这片土地上的财产。古志有载:“郛堤城在(盐山)县北七十五里,又名合骑城,汉公孙敖封合骑侯即此”“西汉武帝元朔四年于此置合骑侯国,称合骑城”“作伏猗城,云防猗卢而设”。还有史载:公孙敖三从大将军卫青击匈奴,元朔五年,因战功封合骑侯,食邑一千五百户。
综上可知,郛堤城应是合骑侯公孙敖封地之城。汉武帝雄才大略,自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他心目中,开疆扩土是帝王的天职,华夏大地每一寸土地都是珍贵的,容不得异族的侵扰。辽阔的渤海沿岸地带,虽荒僻,但有鱼盐资源之富,正需要公孙敖这样的战将镇守。郛堤城,当地老百姓称为武帝城,郛堤之称由来,《同治志》称其为“郛堤之号似即伏猗之讹音也”,“伏猗”当指降伏猗卢。可以想见,当年数千百姓在此挖黏土抬上城上,架夯而筑,黏土层层加高,汉子们挥汗如雨。公孙敖披挂坚甲,左手扶住腰上的利剑,站立城上向北瞭望,黄河在城北向东流去,他一脸忧心忡忡,北风扬起他背上蓝色的披风。两年后的一天夜里,北狄的一支大军越过黄河,偷袭这座土城,守军拼死御敌,怎奈兵力不及北狄,兵败城毁。
古城为正方形,每边一里之多,两千年的风狂雨骤下,城高依然五六米,最高处有七八米之高。近年发掘,郛堤城并非汉代始建,战国时期即有城墙,汉武帝时封侯复修,直至隋唐时仍有遗迹。郛堤城在兵燹后的凄风苦雨中荒芜下来,而这一荒芜就是二千年。野草荆棘环绕中,百姓们在城内开荒种地,盐碱贫瘠的土地也带来一些收获的喜悦。
走在古城下,荒草丛中坑坑洼洼,有洞穴森森,昔日却是狐狸藏身处,诺大的古城也是它们的家园。亘古以来,那些狐仙的传说从这里不胫而走。人们说:武帝城是狐仙的地方,谁家办婚丧大事,少不了需要盆盆碗碗,人们傍晚到城垣里僻静处烧上一炷香,沿城寻找,就会找到大堆餐厨用具。拉回去用完了,再在傍晚时送回原地,烧香以示谢意即可。谁知有贪财人家,用完不再送还,从此不再应验。又传昔日扣村一个老妪被狐仙接去接生,赠送一把豆子,被她沿途扔掉,次日口袋残留的几粒竟是金豆,以此安度晚年。诸多的传说虽未被蒲松龄收集,但老百姓口中《聊斋》却流传一代又一代。
当地百姓称此古城为武帝城也很自然,当年汉武帝雄心勃勃,欲一统天下,率千军万马来此大海边巡海,登高台祭祀海神,以祈江山永固、国泰民安。由郛堤城向东20里处,兀立一座土台,即是赫赫有名的武帝台。史籍有载:“章武县东百里有武帝台……俗云汉武帝东巡海上所筑。”
数十年间,我曾多次登临此台,夏季,沿北坡斜上,草深绊脚,枣刺挂衣。台顶平坦,残砖散落。人说多年前台高20余米,台顶原有小神庙,即蚂蚱神庙。相传汉将刘猛奉旨率军来此海湾灭蝗,蝗虫未灭,刘猛自觉无颜复命蹈海而亡。皇帝感其诚,封刘猛为蚂蚱神,百姓不忘这位忠诚无二将军,修庙祭祀。武帝台之北即齐、燕交界之地,此台原为军事烽火台,汉武帝元狩二年在此地基上筑高台而成。
时代更迭,巨台已非旧时面目,周边平整的土地上庄稼繁茂,落下孤零零一座小土丘。古城沉睡,直至2016年,城外西北发现1千余座瓮棺葬,发掘100余座,那些瓮棺或圆头长圆身,或圆筒形相拼接,苦盐水的浸泡、寒冬的冰冻、土层的挤压,许多瓮棺碎裂,已是道道裂痕,各种形状的陶制瓮棺保存更多的是儿童的骸骨。战国、汉代早期的二三百年间的苦海沿边,缺少木材,以陶制做葬具对病亡的儿童和成人已经是最好的归宿了。
大海东去,沧海桑田,人们在洪水中搏击奋争、在蝗灾中与害虫拼杀、在匪患中与恶匪抢回生存的权利。前赴后继,守候家园。当如狼似虎的日寇把魔爪伸进了这片土地时,抗日的军民奋然而起,八年间,用生命和鲜血勇敢地捍卫了这片土地的尊严。黄骅,一个把足迹印在万里长征路上的将领,倒在叛徒罪恶的枪弹下,血色染红这片英雄的土地,他的名字镌刻在广袤的海湾。
又一个春夏之交,我踏着褐红的木栈道走进郛堤城,路旁月季花红花黄,黄蓿蓬蓬密集,城下的青草已掩盖了去岁的萎黄,把土墙护卫成一个绿色的方阵。城中枯黄芦苇已扬尽生命的种子,根下的新苇即将越过高挑的残秸。石碑河畔,已是芦苇摇曳的公园,有灰麻的野鸭在静水中游动,时而钻进苇丛,时而潜水寻鱼。几只白鹭翩然而起,沿河向西。古城周边,楼宇高耸,挂着蓝天的云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