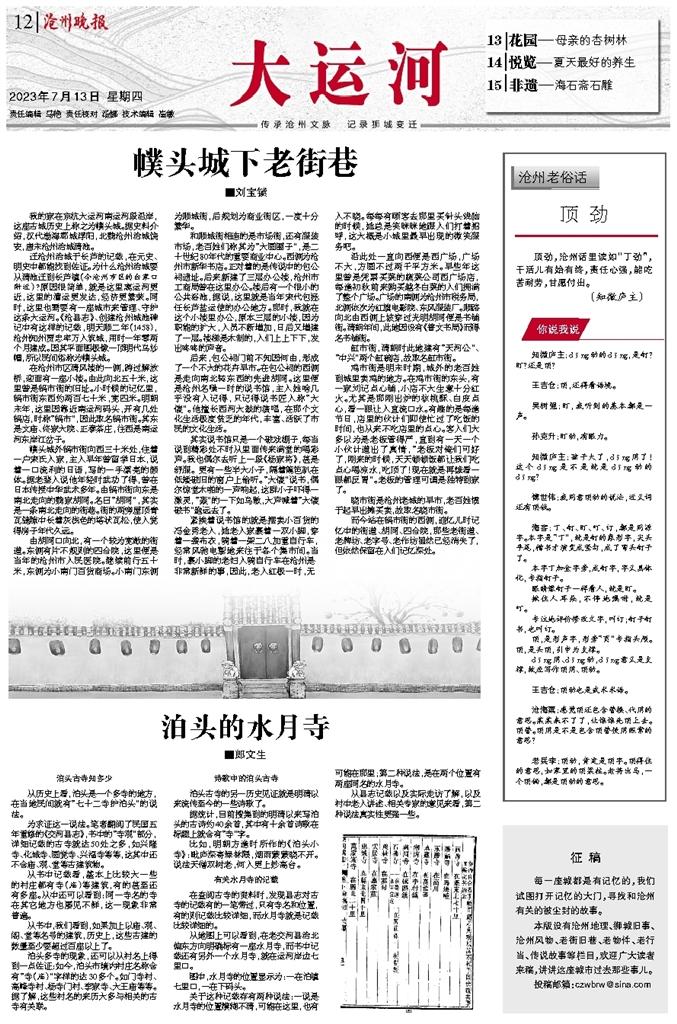我的家在京杭大运河南运河段沿岸,这座古城历史上称之为幞头城。据史料介绍,汉代渤海郡城浮阳,北魏沧州治城饶安,唐末沧州治城清池。
迁沧州治城于长芦的记载,在元史、明史中都能找到佐证。为什么沧州治城要从清池迁到长芦镇(今沧州市区的白家口附近)?原因很简单,就是这里离运河更近,这里的漕运更发达,经济更繁荣。同时,这里也需要有一座城市来管理、守护这条大运河。《沧县志》、创建沧州城池碑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明天顺二年(1458),沧州知州贾忠率万人筑城,用时一年零两个月建成。因其平面图极像一顶明代乌纱帽,所以民间俗称为幞头城。
在沧州市区清风楼的一侧,跨过解放桥,迎面有一座小楼。由此向北五十米,这里曾是锅市街的旧址。小时候的记忆里,锅市街东西约两百七十米,宽四米。明朝末年,这里因靠近南运河码头,开有几处锅店,时称“锅市”,因此取名锅市街。其东是文庙、佟家大院、正泰茶庄,往西是南运河东岸江岔子。
幞头城外锅市街向西三十米处,住着一户宋氏人家,主人早年曾留学日本,说着一口流利的日语,写的一手漂亮的颜体。据老辈人说他年轻时武功了得,曾在日本传授中华武术多年。由锅市街向东是南北走向的魏家胡同。名曰“胡同”,其实是一条南北走向的街巷。街的两旁屋顶青瓦缝隙中长着灰浅色的塔状瓦松,使人觉得房子年代久远。
由胡同口向北,有一个较为宽敞的街道。东侧有片不规则的四合院,这里便是当年的沧州市人民医院。继续前行五十米,东侧为小南门百货商场。小南门东侧为顺城街,后规划为商业街区,一度十分繁华。
和顺城街相连的是市场街,还有服装市场,老百姓们称其为“大圆圈子”,是二十世纪80年代的重要商业中心。西侧为沧州市新华书店。正对着的是传说中的包公祠遗址。后来新建了三层办公楼,沧州市工商局曾在这里办公。楼后有一个很小的公共浴池,据说,这里就是当年宋代包拯任长芦盐运使的办公地方。那时,我就在这个小楼里办公,原本三层的小楼,因为职能的扩大,人员不断增加,日后又增建了一层。楼梯是木制的,人们上上下下,发出咚咚的声音。
后来,包公祠门前不知因何由,形成了一个不大的花卉早市。在包公祠的西侧是走向南北转东西的先进胡同。这里便是沧州名噪一时的说书馆,主人姓啥几乎没有人记得,只记得说书匠人称“大傻”。他擅长西河大鼓的演唱,在那个文化生活极度贫乏的年代,丰富、活跃了市民的文化生活。
其实说书馆只是一个破戏棚子,每当说到精彩处不时从里面传来满堂的喝彩声。我也偶尔去听上一段《杨家将》,甚是舒服。 更有一些半大小子,隔着篱笆趴在低矮破旧的窗户上偷听。“大傻”说书,偶尔惊堂木啪的一声响起,这群小子吓得一激灵,“轰”的一下如鸟散,大声喊着“大傻破书”跑远去了。
紧挨着说书馆的就是摆卖小百货的冯金秀老人,她老人家裹着一双小脚,穿着一袭布衣,骑着一架二八加重自行车,经常风驰电掣地来往于各个集市间。当时,裹小脚的老妇人骑自行车在沧州是非常新鲜的事,因此,老人红极一时,无人不晓。每每有顾客去那里买针头线脑的时候,她总是笑眯眯地跟人们打着招呼,这大概是小城里最早出现的微笑服务吧。
沿此处一直向西便是西广场,广场不大,方圆不过两千平方米。早些年这里曾是凭票买菜的蔬菜公司西广场店,每逢初秋前来购买越冬白菜的人们拥满了整个广场。广场的南侧为沧州市税务局,北侧依次为红旗电影院、东风服装厂。顺路向北由西侧上坡穿过光明胡同便是书铺街。清朝年间,此地因设有《普文书局》而得名书铺街。
缸市街,清朝时此地建有“天河公”、“中兴”两个缸碗店,故取名缸市街。
鸡市街是明末时期,城外的老百姓到城里卖鸡的地方。在鸡市街的东头,有一家刘记点心铺,小店不大生意十分红火。尤其是那刚出炉的核桃酥、白皮点心,看一眼让人直流口水。有趣的是每逢节日,店里的伙计们即使忙过了吃饭的时间,也从来不吃店里的点心。客人们大多以为是老板管得严,直到有一天一个小伙计道出了真情,“老板对俺们可好了,刚来的时候,天天顿顿饭都让我们吃点心喝凉水,吃顶了!现在就是再饿看一眼都反胃”。老板的管理可谓是独特到家了。
晓市街是沧州老城的早市,老百姓惯于起早出摊买卖,故取名晓市街。
而今站在锅市街的西侧,追忆儿时记忆中的街道、胡同、四合院,那些老街道、老牌坊、老字号、老作坊虽然已经消失了,但依然保留在人们记忆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