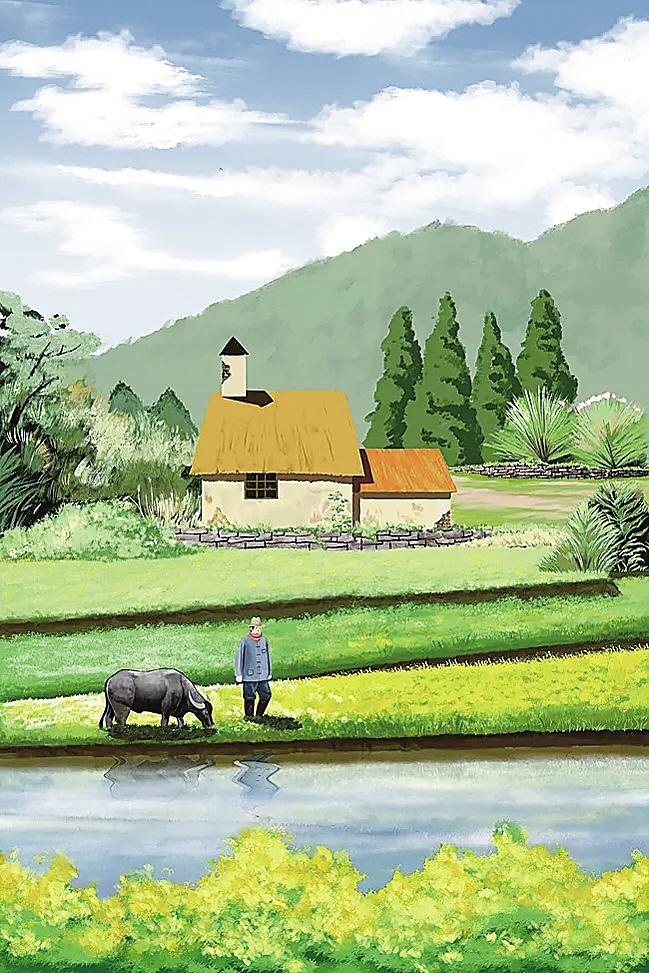早晨,随着几声渺远的鸡鸣,村子醒来了。随后,大大小小的柴门吱吱呀呀响了起来,间或夹杂几声狗吠和主人的斥责。然后,扁担、水桶伴随着咕咚咕咚的脚步声唱起来。它们的歌声一唱一和,将村子唱亮了,将水井唱乐了,将家家户户的炊烟唱直了。
柴火在灶膛跳跃,半开的水在大锅中喧嚣,勤劳的家庭主妇在灶台上的黑缸盆里掬起一捧金黄柔软的玉米面,轻轻几下将它们拍成一个镶嵌着指印的圆饼。瞅准位置,气定神闲地一甩,“啪”的一声,那黄灿灿的玉米面饼子便服服贴贴地趴在了锅壁上。盖上锅盖,坐到灶前,拉动风箱,风箱“呼嗒呼嗒”的,给灶膛中的柴火助威,给房顶上冲天而上的烟柱造势。
十几分钟后,饭熟了,风箱声慢慢停下来,房顶上的炊烟柱越来越细。直到一缕炊烟也没有了,太阳的第一束光就来到了烟火气息浓郁的村子里。
你听,家家户户被放出来的母鸡“咕咕”叫着找食。公鸡先昂首挺胸拍几下翅膀,又乍起脖子上的羽毛,伸脖收颈,来几声嘹亮的长鸣。在它们的聒噪声中,主妇们用玉米面、麦麸和好了鸡食,食盆往院中央一蹾,公鸡母鸡们一拥而上,你啄我抢。
上午,村中的大人下地,小孩上学,鸡鸭猫狗猪崽羊羔马驹牛犊各自在自己的天地里玩耍嬉戏。声音最响亮的还数老母鸡,它们在窗台上的麦秸窝里下了蛋,惟恐天下不知,一只只“咯咯哒”地将自己的功绩昭告世界。
中午,村里人大多在家,串乡做小买卖的舍不得放过这段黄金时间。卖大豆腐的来了,在胡同口“梆梆”地敲梆子;卖香油麻汁的来了,在大柳树下“当当”地敲铜盘,有时还亮开嗓子拉长声来一句——香油麻汁;卖酱油甜醋的来了,脖子上绷着青筋吆喝,“打青酱甘醋咧,打青酱甘醋咧”……
黄昏,马驹、牛犊也不再在外面疯跑。偶尔有羊羔子走错了门,它们的主人就爬到房顶上大声发布寻物启事:“跑谁家一个羊羔子去啊,鼻子上有俩黑点儿,脖子下头有俩肉耷拉儿,要跑你家去,你言语声!”一遍播完,再播一遍。一般情况下,喊不过三遍,走错门的羊羔子就被送回了家里。
村庄的声音从早到晚,从春到冬,年年岁岁,周而复始。那些氤氲着烟火气息的村庄天籁让人心暖,让人留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