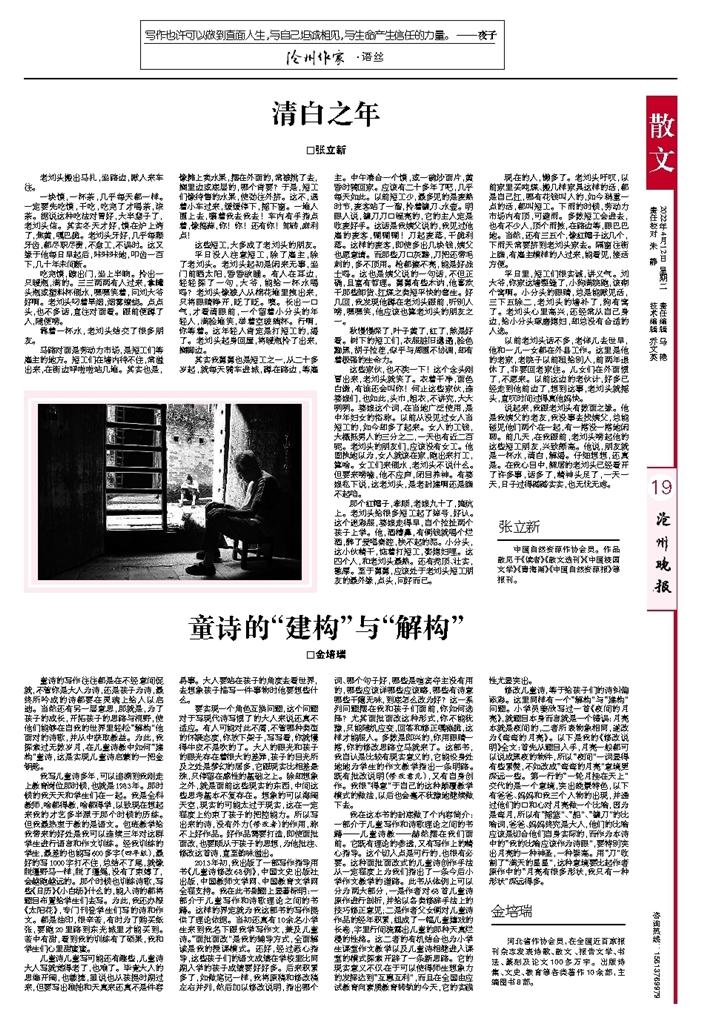童诗的写作往往都是在不经意间促就,不管你是大人为诗,还是孩子为诗,最终所吟成的诗都要在灵魂上给人以启迪。当然还有另一层意思,那就是,为了孩子的成长,开拓孩子的思路与视野,使他们能够在自我的世界里轻松“解构”他面对的诗歌,并从中获取教益。为此,我探索过无数岁月,在儿童诗教中如何“建构”童诗,这是实现儿童诗启蒙的一把金钥匙。
我写儿童诗多年,可以追溯到我刚走上教育岗位那时候,也就是1983年。那时候的我天天和学生们在一起。我是全科教师,啥都得教,啥都得学,以致现在想起来我的才艺多半源于那个时候的历练。但我最热衷于教的是语文。包班教学给我带来的好处是我可以连续三年对这群学生进行语言和作文训练。经我训练的学生,最差的也能写600多字(四年级),最好的写1000字打不住,总结不了尾,就像脱缰野马一样,脱了缰绳,没有了束缚了,会越跑越远的。那个时候也训练诗歌,写些《日历》《小白杨》什么的,能入诗的都将题目布置给学生们去写。为此,我还办报《太阳花》,专门刊登学生们写的诗和作文。都是油印,很辛苦,有时为了购买纸张,要跑20里路到东光城里才能买到。苦中有甜,看到我的训练有了硕果,我和学生们心里甜蜜蜜。
儿童诗儿童写可能还有趣些,儿童诗大人写就觉得老了,也难了。毕竟大人的思维开阔,也敏捷,虽说也从孩提时期过来,但要写出稚拙和天真来还真不是件容易事。大人要站在孩子的角度去看世界,去想象孩子描写一件事物时他要想些什么。
要实现一个角色互换问题,这个问题对于写现代诗写惯了的大人来说还真不适应。有人可能对此不屑,不管哪种类型的怀疑态度,你放下架子,写写看,你就懂得牛皮不是吹的了。大人的眼光和孩子的眼光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孩子的目光所及之处是梦幻的居多,它跟现实比相差悬殊,只停留在感性的基础之上。除却想象之外,就是面前这些现实的东西,中间这些思考基本不复存在。想象的可以海阔天空,现实的可能太过于现实,这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孩子的把控能力。所以写出来的诗,没有外力(修改者)的作用,称不上好作品。好作品需要打造,即使面批面改,也要顺从于孩子的思想,为他批注、修改这首诗,直至韵味溢出。
2013年初,我出版了一部写作指导用书《儿童诗修改68例》,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中国教师文学网、中国教育文学网全程支持。我在此书副题上显著标明:一部介于儿童写作和诗歌理论之间的书籍。这样的界定就为我这部书的写作提供了理论依据。当初还真有10余名小学生来到我名下跟我学写作文,兼及儿童诗。“面批面改”是我的辅导方式,全面解读是我的授课模式。还好,经过悉心指导,这些孩子们的语文成绩在学校里比同期入学的孩子成绩要好好多。后来积累多了,如做笔记一样,我将原稿和修改稿左右并列,然后加以修改说明,指出哪个词、哪个句子好,哪些是喧宾夺主没有用的,哪些应该详哪些应该略,哪些有诗意哪些干瘪无味,到底怎么改为好?这一系列问题摆在我和孩子们面前,你如何选择?尤其面批面改这种形式,你不能犹豫,只能随机应变,回答和修正嘎嘣脆,这样才能服人。多数是即兴的,你用眼睛一搭,你的修改思路立马就来了。这部书,我自认是比较有现实意义的,它能设身处地地为学生的作文教学指出一条明路。既有批改说明(修改意见),又有自身创作。我很“得意”于自己的这种颠覆教学模式的做法,以后也会毫不犹豫地继续做下去。
我在这本书的封底做了个内容简介:一部介于儿童写作和诗歌理论之间的书籍——儿童诗教——赫然摆在我们面前。它既有理论的参透,又有写作上的精心指导。这个切入点是可行的,也很有必要。这种面批面改式的儿童诗创作手法从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指出了一条今后小学作文教学的道路。此书从体例上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作者对68首儿童诗原作进行剖析,并给以各类修辞手法上的技巧修正意见;二是作者父女俩对儿童诗作品的经年积累,组成了一幅儿童嬉戏的长卷,字里行间流露出儿童的那种天真烂漫的性格。这二者的有机结合也为小学生课堂作文教学以及儿童诗相继进入课堂的模式探索开辟了一条新思路。它的现实意义不仅在于可以使得师生想象力的发挥达到“互惠互利”,而且在全国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的今天,它的实践性尤显突出。
修改儿童诗,等于给孩子们的诗纠偏添彩。这里同样有一个“解构”与“建构”问题。小学员姜欣写过一首《夜间的月亮》,就题目本身而言就是一个错误:月亮本就是夜间的,二者所表物象相同,遂改为《弯弯的月亮》。以下是我的《修改说明》全文:首先从题目入手,月亮一般都可以说成黑夜的物件,所以“夜间”一词显得有些累赘,不如改成“弯弯的月亮”意境更深远一些。第一行的“一轮月挂在天上”交代的是一个意境,突出晚景特色,以下有爸爸、妈妈和我三个人物的出现,并通过他们的口和心对月亮做一个比喻,因为是弯月,所以有“摇篮”、“船”、“镰刀”的比喻词,爸爸、妈妈终究是大人,他们的比喻应该是切合他们自身实际的,而作为本诗中的“我的比喻应该作为诗眼”,要特别突出月亮的一种神圣,一种崇高。用“刀”收割了“满天的星星”,这种意境要比起作者原作中的“月亮有很多形状,我只有一种形状”深远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