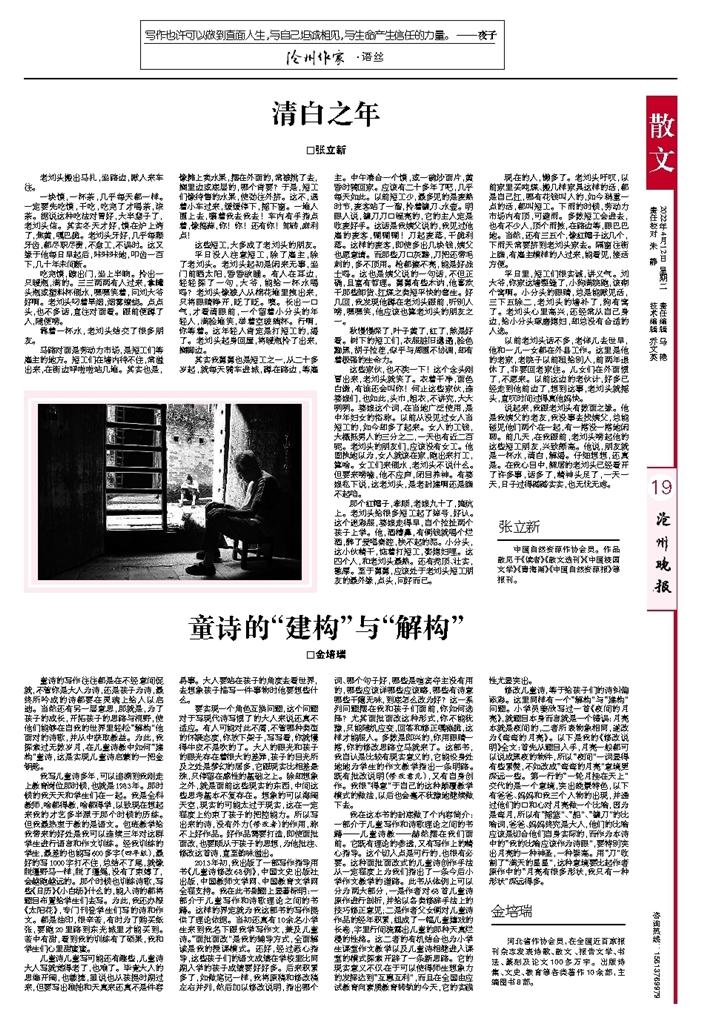老刘头搬出马扎,坐路边,瞅人来车往。
一块馍,一杯茶,几乎每天都一样。一定要先吃馍,干吃,吃完了才喝茶,浓茶。据说这种吃法对胃好,大半辈子了,老刘头信。其实冬天才好,馍在炉上烤了,焦黄,嘎巴脆。老刘头牙好,几乎每颗牙齿,都尽职尽责,不怠工,不误时。这又缘于他每日早起后,咔咔咔地,叩齿一百下,几十年未间断。
吃完馍,踱出门,坐上半晌。拎出一只暖瓶,满的。三三两两有人过来,拿罐头瓶或塑料杯倒水,嘿嘿笑着,问刘大爷好啊。老刘头叼着旱烟,烟雾缭绕。点点头,也不多话,直往对面看。跟前便蹲了人,随便唠。
靠着一杯水,老刘头结交了很多朋友。
马路对面是劳动力市场,是短工们等雇主的地方。短工们在墙内待不住,常溢出来,在街边呼啦啦站几堆。其实也是,像摊上卖水果,摆在外面的,常被挑了去,搁里边或底层的,哪个肯要?于是,短工们像待售的水果,使劲往外挤。这不,遇着小车过来,缓缓停下,摇下窗。一堆人围上去,嚷着我去我去!车内有手指点着,像捣蒜,你!你!还有你!卸砖,麻利点!
这些短工,大多成了老刘头的朋友。
平日没人注意短工,除了雇主,除了老刘头。老刘头起初是闲来无事,坐门前晒太阳,昏昏欲睡。有人在耳边,轻轻探了一句,大爷,能给一杯水喝吗?老刘头像被人从棉花堆里拽出来,只将眼睛睁开,眨了眨。噢。长出一口气,才看清眼前,一个留着小分头的年轻人,满脸堆笑,举着空玻璃杯。行啊,你等着。这年轻人肯定是打短工的,渴了。老刘头起身回屋,将暖瓶拎了出来,搁脚边。
其实我舅舅也是短工之一,从二十多岁起,就每天骑车进城,蹲在路边,等雇主。中午凑合一个馍,或一碗炒面片,黄昏时骑回家。应该有二十多年了吧,几乎每天如此。以前短工少,最多见的是麦熟时节,麦客站了一溜,拎着镰刀、水壶。明眼人说,镰刀刀口锃亮的,它的主人定是收麦好手。这话是我姨父说的,我见过他雇的麦客,唰唰唰!刀起麦落,干脆利落。这样的麦客,即使多出几块钱,姨父也愿意请。而那些刀口灰黯,刀把还带毛刺的,多不顶用。枪都擦不亮,能是好战士吗。这也是姨父说的一句话,不但正确,且富有哲理。舅舅有些木讷,他喜欢干那些卸货、扛煤之类短平快的营生。好几回,我发现他蹲在老刘头跟前,听别人唠,嘿嘿笑,他应该也算老刘头的朋友之一。
秋慢慢深了,叶子黄了,红了,煞是好看。树下的短工们,衣服脏旧邋遢,脸色黝黑,胡子拉茬,似乎与周围不协调,却有着极强的生命力。
这些家伙,也不洗一下!这个念头刚冒出来,老刘头就笑了。衣着干净,面色白嫩,有谁还会叫你!何止这些家伙,连婆娘们,也如此,头巾,粗衣,不讲究,大大咧咧。婆娘这个词,在当地广泛使用,是中年妇女的俗称。以前从没见过女人当短工的,如今却多了起来。女人的工钱,大概抵男人的三分之二,一天也有近二百呢。老刘头的朋友们,应该没有女工。他固执地以为,女人就该在家,跑出来打工,算啥。女工们来倒水,老刘头不说什么。但要来唠嗑,他不应声,闭目养神。有婆娘私下说,这老刘头,是老封建啊还是瞧不起咱。
那个红帽子,孝顺,老娘九十了,瘫炕上。老刘头给很多短工起了绰号,好认。这个迷彩服,婆娘走得早,自个拉扯两个孩子上学。他,酒糟鼻,有俩钱就喝个烂酒,醉了爱唱秦腔,扶不起的泥。小分头,这小伙精干,惦着打短工,娶媳妇哩。这四个人,和老刘头最熟。还有秃顶、壮实,憨厚。至于舅舅,应该处于老刘头短工朋友的最外缘,点头,问好而已。
现在的人,懒多了。老刘头吁叹,以前家里买吨煤、搬几样家具这样的活,都是自己扛,哪有花钱叫人的,如今稍重一点的活,都叫短工。下雨的时候,劳动力市场内有顶,可避雨。多数短工会进去,也有不少人,顶个雨披,在路边等,眼巴巴地。当然,还有三五个,像红帽子这几个,下雨天常要挤到老刘头家去。隔窗往街上瞧,有雇主模样的人过来,能看见,接活方便。
平日里,短工们很实诚,讲义气。刘大爷,你家这墙裂缝了,小狗满院跑,该砌个窝啊。小分头的眼睛,总是能瞅见活,三下五除二,老刘头的墙补了,狗有窝了。老刘头心里高兴,还经常从自己身边,给小分头琢磨媳妇,却总没有合适的人选。
以前老刘头话不多,老伴儿去世早,他和一儿一女都在外县工作。这里是他的老家,老院子以前租给别人,前两年退休了,非要回老家住。儿女们在外面惯了,不愿来。以前这边的老伙计,好多已经走到他前边了,想到这事,老刘头就摇头,直叹时间过得真他妈快。
说起来,我跟老刘头有数面之缘。他是我姨父的老友,我没事去找姨父,总能碰见他们两个在一起,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前几天,在我跟前,老刘头唠起他的这些短工朋友,兴致颇高。他说,朋友就是一杯水,清白,解渴。仔细想想,还真是。在我心目中,鳏居的老刘头已经看开了许多事,话多了,精神头足了,一天一天,日子过得踏踏实实,也无忧无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