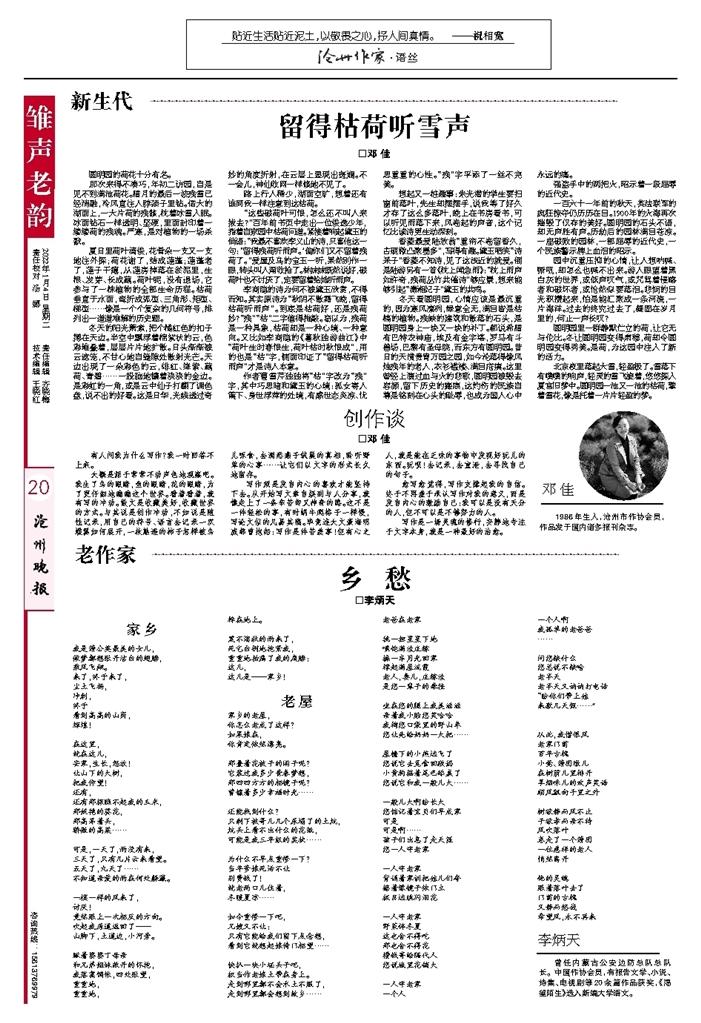圆明园的荷花十分有名。
那次来得不凑巧,年初二访园,自是见不到满池荷花。腊月的最后一波残雪已经消融,冷风直往人脖颈子里钻。偌大的湖面上,一大片荷的残骸,枕着冰雪入眠。冰面钻石一样透明、坚硬,里面封印着一缕缕荷的残魂。严寒,是对植物的一场杀戮。
夏日里荷叶清俊,花骨朵一支又一支地往外探;荷花谢了,结成莲蓬;莲蓬老了,莲子干瘪,从莲房掉落在淤泥里,生根、发芽、长成藕。荷叶呢,没有退场,它参与了一株植物的全部生命历程。枯荷垂直于水面,弯折成弧型、三角形、矩型、梯型……像是一个个复杂的几何符号,排列出一道道难解的历史题。
冬天的阳光萧索,把个橘红色的扣子摁在天边。半空中飘浮着棉絮状的云,色彩堆叠着,层层片片地扩散。日头渐渐被云遮笼,不甘心地自缝隙处散射光芒。天边出现了一朵彩色的云,绯红、绛紫、藕荷、青碧……一股脑地镶着淡淡的金边。是彩虹的一角,或是云中仙子打翻了调色盘,说不出的好看。这是日华,光线透过奇妙的角度折射,在云层上显现出斑斓。不一会儿,神仙收网一样倏地不见了。
路上行人稀少,湖面空旷,想着还有谁同我一样注意到这枯荷。
“这些破荷叶可恨,怎么还不叫人来拔去?”百年前书页中走出一位俊逸少年,指着自家园中枯荷问道。紧接着响起黛玉的俏语:“我最不喜欢李义山的诗,只喜他这一句:‘留得残荷听雨声。’偏你们又不留着残荷了。”爱屋及乌的宝玉一听,果然别作一眼,转头叫人甭收拾了。林妹妹既然说好,破荷叶也不讨厌了,定要留着给她听雨声。
李商隐的诗为何不被黛玉欣赏,不得而知。其实原诗为“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到底是枯荷好,还是残荷妙?“残”“枯”二字值得推敲。窃以为,残荷是一种具象,枯荷却是一种心境、一种意向。又比如李商隐的《暮秋独游曲江》中“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用的也是“枯”字,侧面印证了“留得枯荷听雨声”才是诗人本意。
作者曹雪芹独独将“枯”字改为“残”字,其中巧思暗和黛玉的心境:孤女寄人篱下、身世浮萍的处境,有感世态炎凉、忧思重重的心性。“残”字平添了一丝不完美。
想起又一桩趣事:朱光潜的学生要扫窗前落叶,先生却摆摆手,说我等了好久才存了这么多落叶,晚上在书房看书,可以听见雨落下来,风卷起的声音,这个记忆比读诗更生动深刻。
香菱最爱陆放翁“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凸聚墨多”,写得有趣。黛玉哂笑“诗呆子”香菱不知诗,见了这浅近的就爱。倒是陆游另有一首《枕上闻急雨》:“枕上雨声如许奇,残荷丛竹共催诗”够应景,想来能够引起“潇湘妃子”黛玉的共鸣。
冬天看圆明园,心情应该是最沉重的,因为寒风凛冽,绿意全无,满目皆是枯槁的植物。残缺的建筑和散落的石头,是圆明园身上一块又一块的补丁。都说希腊有巴特农神庙,埃及有金字塔,罗马有斗兽场,巴黎有圣母院,而东方有圆明园。昔日的天潢贵胄万园之园,如今沦落得像风烛残年的老人,衣衫褴褛、满目疮痍。这里曾经上演过血与火的悲歌,圆明园被毁去容颜,留下历史的瘢痕,这灼伤的民族自尊是铭刻在心头的耻辱,也成为国人心中永远的痛。
强盗手中的两把火,昭示着一段屈辱的近代史。
一百六十一年前的秋天,英法联军的疯狂掠夺仍历历在目。1900年的火海再次摧毁了仅存的美好。圆明园的石头不语,却无声胜有声。历劫后的园林满目苍凉。一座破败的园林,一部屈辱的近代史,一个民族警示牌上血泪的昭示。
园中沉重压抑的心情,让人想呐喊、嘶吼,却怎么也喊不出来。游人眼望着黑白灰的世界,或低声叹气,或咒骂着侵略者和破坏者,或怆然似要落泪。悲悯的目光积攒起来,怕是能汇聚成一条河流,一片海洋。过去的终究过去了,凝固在岁月里的,何止一声长叹?
圆明园里一群静默伫立的荷,让它无与伦比。冬让圆明园变得肃穆,荷却令圆明园变得秀美。是荷,为这园中注入了新的活力。
北京夜里落起大雪,轻盈极了。雪落下有噗噗的响声,轻灵的雪飞旋着,悠悠探入夏宫旧梦中。圆明园一池又一池的枯荷,擎着雪花,像是托着一片片轻盈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