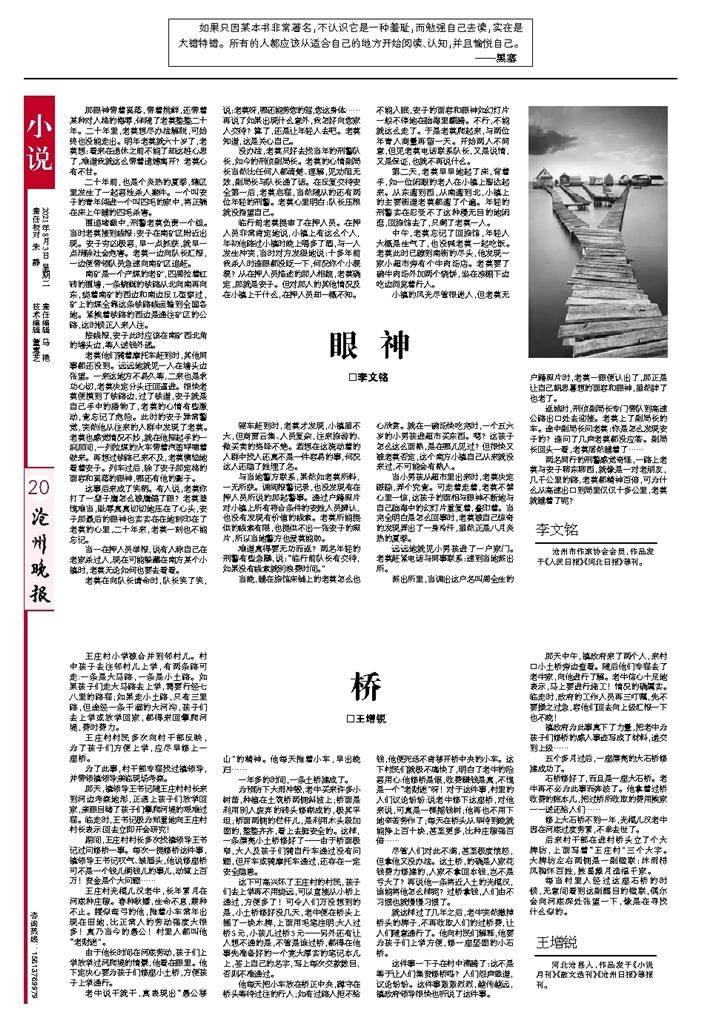王庄村小学被合并到邻村儿。村中孩子去往邻村儿上学,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大马路,一条是小土路。如果孩子们走大马路去上学,需要行经七八里的路程;如果走小土路,只有三里路,但途经一条干涸的大河沟,孩子们去上学或放学回家,都得来回攀爬河堤,费时费力。
王庄村村民多次向村干部反映,为了孩子们方便上学,应尽早修上一座桥。
为了此事,村干部专程找过镇领导,并带领镇领导亲临现场考察。
那天,镇领导王书记随王庄村村长来到河边考察地形,正遇上孩子们放学回家,亲眼目睹了孩子们攀爬河堤的艰难过程。临走时,王书记极为郑重地向王庄村村长表示:回去立即开会研究!
期间,王庄村村长多次找镇领导王书记过问修桥一事。每次一提修桥这件事,镇领导王书记叹气、皱眉头,他说修座桥可不是一个钱儿俩钱儿的事儿,动辄上百万!资金是个大问题……
王庄村光棍儿汉老牛,长年累月在河底种庄稼。春种秋播,生命不息,耕种不止。腰似弯弓的他,推着小车常年出现在田地,比正常人的劳动强度大很多!真乃当今的愚公!村里人都叫他“老财迷”。
由于他长时间在河底劳动,孩子们上学放学过河爬堤的情景,他看在眼里。他下定决心要为孩子们修座小土桥,方便孩子上学通行。
老牛说干就干,真表现出“愚公移山”的精神。他每天推着小车,早出晚归……
一年多的时间,一条土桥建成了。
为预防下大雨冲毁,老牛买来许多小树苗,种植在土筑桥两侧斜坡上;桥面是利用别人废弃的砖头修砌成的,极其平坦;桥面两侧的栏杆儿,是利用木头段加固的,整整齐齐,看上去挺安全的。这样,一条漂亮小土桥修好了——由于桥面极窄,大人及孩子们骑自行车通过没有问题,但开车或骑摩托车通过,还存在一定安全隐患。
这下可高兴坏了王庄村的村民,孩子们去上学再不用绕远,可以直接从小桥上通过,方便多了!可令人们万没想到的是,小土桥修好没几天,老牛便在桥头上插了一块木牌,上面用毛笔注明:大人过桥5元,小孩儿过桥3元——另外还有让人想不通的是,不管是谁过桥,都得在他事先准备好的一个宽大厚实的笔记本儿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写上每次交款数目,否则不准通过。
他每天把小车放在桥正中央,蹲守在桥头等待过往的行人;如有过路人拒不给钱,他便死活不肯移开桥中央的小车。这下村民们就极不痛快了,明白了老牛的险恶用心:他修桥是假,收费赚钱是真,不愧是一个“老财迷”呀!对于这件事,村里的人们议论纷纷:说老牛修下这座桥,对他来说,可真是一棵摇钱树;他再也不用下地辛苦劳作了;每天在桥头从早待到晚就能挣上百十块,甚至更多,比种庄稼强百倍……
尽管人们对此不满,甚至极度愤怒,但拿他又没办法。这土桥,的确是人家花钱费力修建的,人家不拿回本钱,岂不是亏大了?再说他一条将近入土的光棍汉,谁能将他怎么样呢?过桥拿钱,人们由不习惯也就慢慢习惯了。
就这样过了几年之后,老牛突然撤掉桥头的牌子,不再收取人们的过桥费,让人们随意通行了。他向村民们解释,他要为孩子们上学方便,修一座坚固的小石桥。
这件事一下子在村中沸腾了:这不是等于让人们集资修桥吗?人们怨声载道,议论纷纷。这件事轰轰烈烈,越传越远,镇政府领导很快也听说了这件事。
那天中午,镇政府来了两个人,来村口小土桥旁边查看。随后他们专程去了老牛家,向他进行了解。老牛信心十足地表示,马上要进行施工!情况的确属实。临走时,政府的工作人员再三叮嘱,先不要操之过急,容他们回去向上级汇报一下也不晚!
镇政府为此事真下了力量,把老牛为孩子们修桥的感人事迹写成了材料,递交到上级……
五个多月过后,一座漂亮的大石桥修建成功了。
石桥修好了,而且是一座大石桥。老牛再不必为此事而奔波了。他拿着过桥收费的账本儿,把过桥所收取的费用挨家一一送还给人们……
修上大石桥不到一年,光棍儿汉老牛因在河底过度劳累,不幸去世了。
后来村干部在进村桥头立了个大牌坊,上面写着“王庄村”三个大字。大牌坊左右两侧是一副楹联:沐雨栉风胸怀百姓,披星戴月造福千家。
每当村里人经过这座石桥的时候,无意间看到这副醒目的楹联,偶尔会向河底深处张望一下,像是在寻找什么似的。
王增锐
河北沧县人,作品发于《小说月刊》《散文选刊》《沧州日报》等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