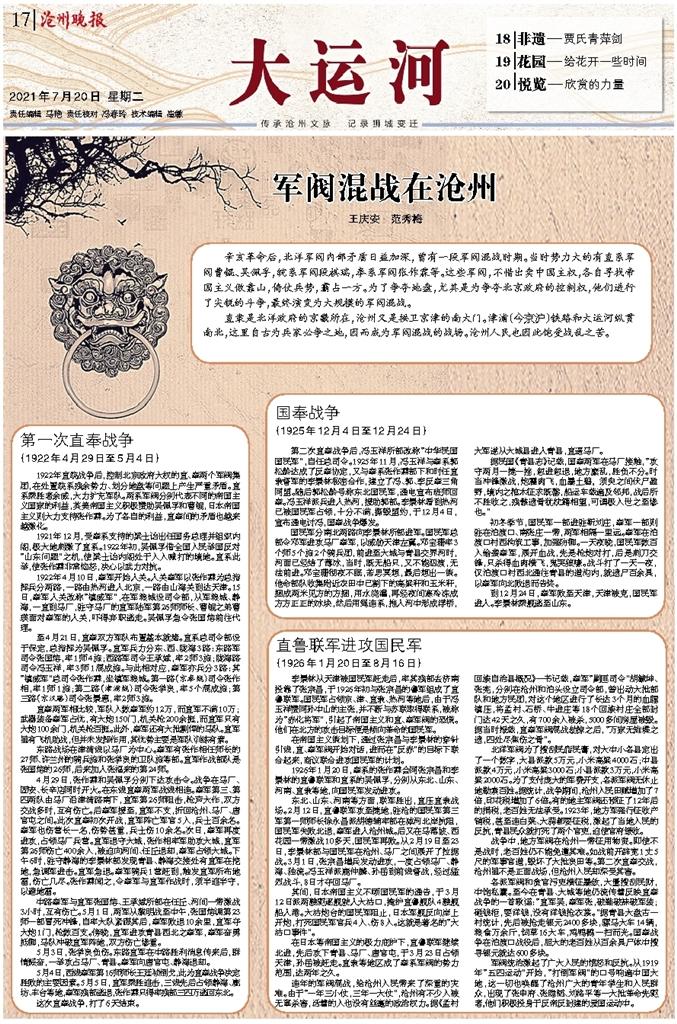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内部矛盾日益加深,曾有一段军阀混战时期。当时势力大的有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皖系军阀段祺瑞,奉系军阀张作霖等。这些军阀,不惜出卖中国主权,各自寻找帝国主义做靠山,倚仗兵势,霸占一方。为了争夺地盘,尤其是为争夺北京政府的控制权,他们进行了尖锐的斗争,最终演变为大规模的军阀混战。
直隶是北洋政府的京畿所在,沧州又是拱卫京津的南大门。津浦(今京沪)铁路和大运河纵贯南北,这里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因而成为军阀混战的战场。沧州人民也因此饱受战乱之苦。
第一次直奉战争
(1922年4月29日至5月4日)
1922年直皖战争后,控制北京政府大权的直、奉两个军阀集团,在处置皖系残余势力、划分地盘等问题上产生严重矛盾。直系乘胜者余威,大力扩充军队。两系军阀分别代表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英美帝国主义积极赞助吴佩孚和曹锟,日本帝国主义则大力支持张作霖。为了各自的利益,直奉间的矛盾也越来越激化。
1921年12月,受奉系支持的梁士诒出任国务总理并组织内阁,极大地刺激了直系。1922年初,吴佩孚借全国人民举国反对“山东问题”之机,使梁士诒内阁处于人人喊打的境地。直系此举,使张作霖非常恼怒,决心以武力对抗。
1922年4月10日,奉军开始入关。入关奉军以张作霖为总指挥兵分两路,一路由热河进入北京,一路由山海关到达天津。15日,奉军入关改称“镇威军”,在军粮城设司令部,从军粮城、静海,一直到马厂,驻守马厂的直军陆军第26师师长、曹锟之弟曹瑛面对奉军的入关,吓得弃职逃走。吴佩孚急令张国熔前往代理。
至4月21日,直奉双方军队布置基本就绪。直系总司令部设于保定,总指挥为吴佩孚。直军兵力分东、西、陇海3路:东路军司令张国熔,率1师4旅;西路军司令王承斌,率2师3旅;陇海路司令冯玉祥,率3师1混成旅。与此相对应,奉军亦兵分3路:其“镇威军”总司令张作霖,坐镇军粮城。第一路(京奉线)司令张作相,率1师1旅;第二路(津浦线)司令张学良,率5个混成旅;第三路(京汉路)司令张景惠,率2师3旅。
直奉两军相比较,军队人数奉军约12万,而直军不满10万;武器装备奉军占优,有大炮150门,机关枪200余挺,而直军只有大炮100余门,机关枪百挺。此外,奉军还有大批剽悍的马队。直军虽有飞机助战,但并未发挥作用,其优势主要是军队训练有素。
东路战场在津浦线以马厂为中心。奉军有张作相任师长的27师、许兰州的骑兵旅和张学良的卫队旅等部。直军作战部队是张国熔的26师,后来加入张福来的第24师。
4月29日,张作霖和吴佩孚分别下达攻击令。战争在马厂、固安、长辛店同时开火。在东线直奉两军战线相连。奉军第三、第四两队由马厂沿津浦路南下,直军第26师阻击,枪声大作,双方交战多时,互有伤亡。后奉军援至,直军不支,折回沧州、马厂、唐官屯之间。此次直奉初次开战,直军阵亡军官5人,兵士百余名。奉军也伤营长一名,伤势甚重,兵士伤10余名。次日,奉军再度进攻,占领马厂兵营。直军退守大城,张作相率军助攻大城,直军第26师伤亡400余人,被迫向河间、任丘退却,奉军占领大城。下午6时,驻守静海的李景林部发现青县、静海交接处有直军在挖地,急调军进击。直军急退。奉军骑兵1营赶到,触发直军所布地雷,伤亡几尽。张作霖闻之,令奉军与直军作战时,须半追半守,以避地雷。
中路奉军与直军张国熔、王承斌所部在任丘、河间一带激战3小时,互有伤亡。5月1日,两军从黎明战至中午,张国熔调第23师一部冒死冲锋,自率大队紧跟其后,奉军败退10余里,直军夺大炮1门,枪数百支。傍晚,直军进攻青县西北之奉军,奉军奋勇抵御,马队冲破直军阵地,双方伤亡惨重。
5月3日,张学良负伤。东路直军在中路胜利消息传来后,群情振奋,一举攻占马厂、青县。奉军向唐官屯、静海退却。
5月4日,西线奉军第16师师长王廷祯倒戈,此为直奉战争决定胜败的主要因素。5月5日,直军乘胜追击,三线先后占领静海、廊坊、丰台等地,奉军残部逃退,张作霖只得率残部三四万逃回东北。
这次直奉战争,打了6天结束。
国奉战争
(1925年12月4日至12月24日)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冯玉祥所部改称“中华民国国民军”,自任总司令。1925年11月,冯玉祥与奉系郭松龄达成了反奉协定,又与奉系张作霖部下和时任直隶督军的李景林秘密合作,建立了冯、郭、李反奉三角同盟。随后郭松龄号称东北国民军,通电宣布班师回奉。冯玉祥派兵进入热河,援助郭部。李景林看到热河已被国民军占领,十分不满,撕毁盟约,于12月4日,宣布通电讨冯,国奉战争爆发。
国民军分南北两路向李景林所部进军。国民军总部令邓军进攻马厂奉军,以威胁天津左翼。邓宝珊率3个师5个旅2个骑兵团,前进至大城与青县交界河时,河面已经结了薄冰,当时,既无船只,又不能泅渡,无法前进。邓宝珊彻夜不眠,苦思冥想,最后想出一策。他命部队收集附近农田中已割下的高粱秆和玉米秆,捆成两米见方的方捆,用水浇灌,再经夜间寒冷冻成方方正正的冰块,然后用绳连系,推入河中形成浮桥,大军遂从大城县进入青县,直逼马厂。
据民国《青县志》记载,国奉两军在马厂接触,“攻守两月一捷一挫,忽进忽退,地方縻乱,胜负不分。时当冲锋激战,炮震肉飞,血暴土碧, 须臾之间伏尸盈野,境内之棺木征求既罄,船运车载遍及邻邦,战后所不胜收之,残骸遗骨犹枕籍相望,可谓极人世之至惨也。”
初冬季节,国民军一部进驻靳刘庄,奉军一部则驻在泊渡口、南张庄一带,两军相隔一里远。奉军在泊渡口村西构筑工事,加强防御。一天夜晚,国民军数百人偷袭奉军,展开血战,先是枪炮对打,后是刺刀交锋,只杀得血肉横飞,鬼哭狼嚎。战斗打了一天一夜,仅泊渡口村西北通往青县的道沟内,就遗尸百余具,以奉军向北败退而告终。
到12月24日,奉军败至天津,天津被克,国民军进入。李景林乘舰逃至山东。
直鲁联军进攻国民军
(1926年1月20日至8月16日)
李景林从天津被国民军赶走后,率其残部去济南投靠了张宗昌,于1926年初与张宗昌的鲁军组成了直鲁联军。国民军占领京、津、直隶、热河等地后,由于冯玉祥赞同孙中山的主张,并不断与苏联取得联系,被称为“赤化将军”,引起了帝国主义和直、奉军阀的恐慌。他们在北方的攻击目标便是倾向革命的国民军。
在帝国主义策划下,通过张宗昌与李景林的穿针引线,直、奉军阀开始对话,进而在“反赤”的目标下联合起来,商议联合进攻国民军的计划。
1926年1月20日,奉系的张作霖会同张宗昌和李景林的直鲁联军和直系的吴佩孚,分别从东北、山东、河南、直隶等地,向国民军发动进攻。
东北、山东、河南等方面,联军胜出,直压直隶战场。2月12日,直鲁联军攻至捷地,驻沧的国民军第三军第一师师长徐永昌派胡德辅率部在减河北岸抗阻,国民军失败北退,奉军进入沧州城。后又在马落坡、西花园一带激战10多天,国民军再败。从2月19日至23日,李景林部与国民军在沧州、马厂之间展开了拉据战。3月1日,张宗昌增兵发动进攻,一度占领马厂、静海、独流。冯玉祥派鹿仲麟、孙岳到前线督战,经过猛烈战斗,8日才夺回马厂。
其间,日本帝国主义不顾国民军的通告,于3月12日派两艘驱逐舰驶入大沽口,掩护直鲁舰队4艘舰船入港。大沽炮台的国民军阻止,日本军舰反向岸上开炮,打死国民军官兵4人、伤8人。这就是著名的“大沽口事件”。
在日本等帝国主义的极力庇护下,直鲁联军继续北进,先后攻下青县、马厂、唐官屯,于3月23日占领天津,孙岳被赶走。直隶等地区成了奉系军阀的势力范围,达两年之久。
连年的军阀混战,给沧州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由于“一年三小仗,三年一大仗”,沧州有不少人被无辜杀害,活着的人也没有丝毫的政治权力。据《孟村回族自治县概况》一书记载,奉军“剿匪司令”胡毓坤、张宪,分别在沧州和泊头设立司令部,曾出动大批部队和地方民团,对这个地区进行了长达3个月的血腥镇压,将孟村、石桥、牛进庄等18个回族村庄全部封门达42天之久,有700余人被杀,5000多间房屋被毁。据当时报载,直奉军阀混战劫掠之后,“万家无雉堞之遗,四处尽焦伤之骨”。
北洋军阀为了搜刮民脂民膏,对大中小各县定出了一个数字,大县派款5万元,小米高粱4000石;中县派款4万元,小米高粱3000石;小县派款3万元,小米高粱2000石。为了支付庞大的军费开支,各派军阀无休止地勒索百姓。据统计,战争期间,沧州人民田赋增加了7倍,印花税增加了6倍。有的地主军阀还预征了12年后的捐税,老百姓无法承受。1923年,地方军强行征收产销税,甚至连白菜、大蒜都要征税,激起了当地人民的反抗,青县民众就打死了两个官吏,迫使官府缓收。
战争中,地方军阀在沧州一带征用物资。即使不是战时,老百姓仍不能免遭其难。如战前开辟宽1丈5尺的军事官道,毁坏了大批良田等。第二次直奉交战,沧州虽不是正面战场,但沧州人民却深受其害。
各派军阀和贪官污吏横征暴敛,大量搜刮民财,中饱私囊。至今在青县、大城等地仍流传着反映直奉战争的一首歌谣:“直军吴,奉军张,破鞋破袜破军装;砸钱柜,要洋钱,没有洋钱抢衣裳。”据青县大盘古一村统计,先后被抢走银元2400多块,骡马大车14辆,粮食万余斤,饲草16大车,鸡鸭鹅一扫而光。国奉战争在泊渡口战役后,胆大的老百姓从百余具尸体中搜寻银元就达600多块。
军阀统治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愤怒和反抗。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打倒军阀”的口号响遍中国大地,这一切也唤醒了沧州广大的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出现了张申府、张隐韬、刘格平等一大批革命先驱者,他们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