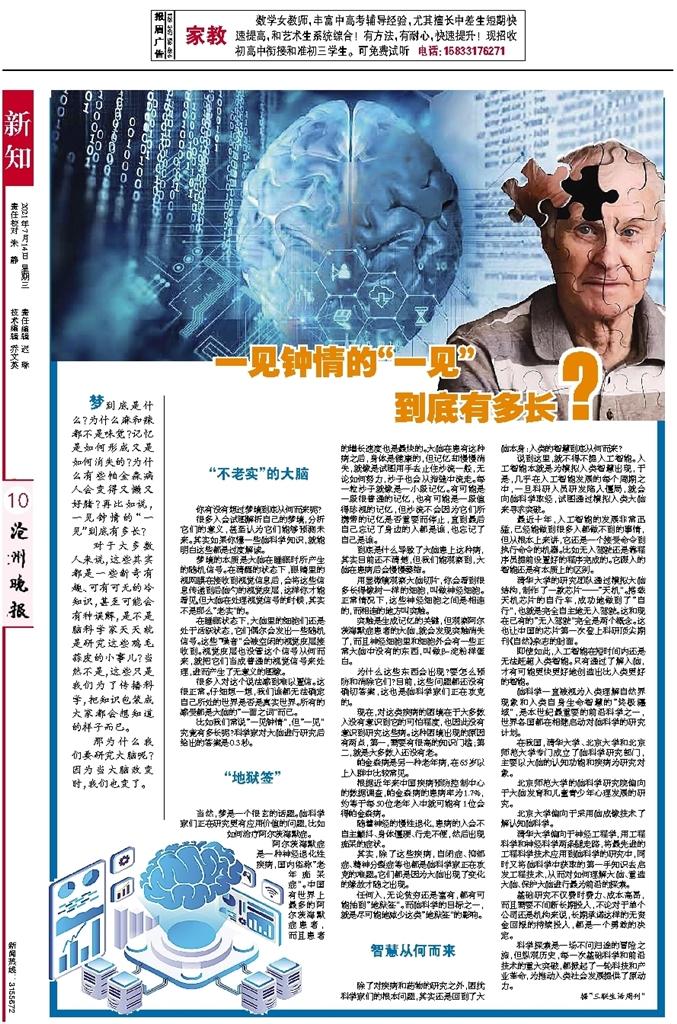到底是什么?为什么麻和辣都不是味觉?记忆是如何形成又是如何消失的?为什么有些帕金森病人会变得又懒又好赌?再比如说,一见钟情的“一见”到底有多长?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些其实都是一些新奇有趣、可有可无的冷知识,甚至可能会有种误解,是不是脑科学家天天就是研究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当然不是,这些只是我们为了传播科学,把知识包装成大家都会想知道的样子而已。
那为什么我们要研究大脑呢?因为当大脑改变时,我们也变了。
“不老实”的大脑
你有没有想过梦境到底从何而来呢?
很多人会试图解析自己的梦境,分析它们的意义,甚至认为它们能够预测未来。其实如果你懂一些脑科学知识,就能明白这些都是过度解读。
梦境的本质是大脑在睡眠时所产生的随机信号。在清醒的状态下,眼睛里的视网膜在接收到视觉信息后,会将这些信息传递到后脑勺的视觉皮层,这样你才能看见,但大脑在处理视觉信号的时候,其实不是那么“老实”的。
在睡眠状态下,大脑里的细胞们还是处于活跃状态,它们偶尔会发出一些随机信号。这些“噪音”会被空闲的视觉皮层接收到。视觉皮层也没管这个信号从何而来,就把它们当成普通的视觉信号来处理,进而产生了无意义的图像。
很多人对这个说法感到难以置信。这很正常。仔细想一想,我们谁都无法确定自己所处的世界是否是真实世界。所有的感受都是大脑的“一面之词”而已。
比如我们常说“一见钟情”,但“一见”究竟有多长呢?科学家对大脑进行研究后给出的答案是0.3秒。
“地狱签”
当然,梦是一个很玄的话题。脑科学家们正在研究更有应用价值的问题,比如如何治疗阿尔茨海默症。
阿尔茨海默症是一种神经退化性疾病,国内俗称“老年痴呆症”。中国有世界上最多的阿尔茨海默症患者,而且患者的增长速度也是最快的。大脑在患有这种病之后,身体是健康的,但记忆却慢慢消失,就像是试图用手去止住沙流一般,无论如何努力,沙子也会从指缝中流走。每一粒沙子就像是一小段记忆。有可能是一段很普通的记忆,也有可能是一段值得珍视的记忆,但沙流不会因为它们所携带的记忆是否重要而停止,直到最后自己忘记了身边的人都是谁,也忘记了自己是谁。
到底是什么导致了大脑患上这种病,其实目前还不清楚,但我们能观察到,大脑在患病后会慢慢萎缩。
用显微镜观察大脑切片,你会看到很多长得像树一样的细胞,叫做神经细胞。正常情况下,这些神经细胞之间是相连的,而相连的地方叫突触。
突触是生成记忆的关键,但观察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大脑,就会发现突触消失了,而且神经细胞里和细胞外会有一些正常大脑中没有的东西,叫做β-淀粉样蛋白。
为什么这些东西会出现?要怎么预防和消除它们?目前,这些问题都还没有确切答案,这也是脑科学家们正在攻克的。
现在,对这类疾病的困境在于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它的可怕程度,也因此没有意识到研究这些病。这种困境出现的原因有两点,第一,需要有很高的知识门槛;第二,就是大多数人还没有老。
帕金森病是另一种老年病,在65岁以上人群中比较常见。
根据近年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调查,帕金森病的患病率为1.7%,约等于每50位老年人中就可能有1位会得帕金森病。
随着神经的慢性退化,患病的人会不自主颤抖、身体僵硬、行走不便,然后出现痴呆的症状。
其实,除了这些疾病,自闭症、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等也都是脑科学家正在攻克的难题。它们都是因为大脑出现了变化的缘故才随之出现。
任何人,无论贫穷还是富有,都有可能抽到“地狱签”。而脑科学的目标之一,就是尽可能地减少这类“地狱签”的影响。
智慧从何而来
除了对疾病和药物的研究之外,困扰科学家们的根本问题,其实还是回到了大脑本身:人类的智慧到底从何而来?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本就是为模拟人类智慧出现,于是,几乎在人工智能发展的每个周期之中,一旦科研人员研发陷入僵局,就会向脑科学取经,试图通过模拟人类大脑来寻求突破。
最近十年,人工智能的发展非常迅猛,已经能做到很多人都做不到的事情,但从根本上来讲,它还是一个接受命令到执行命令的机器。比如无人驾驶还是靠程序员提前设置好的程序完成的。它跟人的智能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
清华大学的研究团队通过模拟大脑结构,制作了一款芯片——“天机”。搭载天机芯片的自行车,成功地做到了“自行”,也就是完全自主地无人驾驶。这和现在已有的“无人驾驶”完全是两个概念。这也让中国的芯片第一次登上科研顶尖期刊《自然》杂志的封面。
即使如此,人工智能在短时间内还是无法赶超人类智能。只有通过了解人脑,才有可能更快更好地创造出比人类更好的智能。
脑科学一直被视为人类理解自然界现象和人类自身生命智慧的“终极疆域”,是本世纪最重要的前沿科学之一,世界各国都在相继启动对脑科学的研究计划。
在我国,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专门成立了脑科学研究部门,主要以大脑的认知功能和疾病为研究对象。
北京师范大学的脑科学研究院偏向于大脑发育和儿童青少年心理发展的研究。
北京大学偏向于采用脑成像技术了解认知脑科学。
清华大学偏向于神经工程学,用工程科学和神经科学两条腿走路,将最先进的工程科学技术应用到脑科学的研究中,同时又将脑科学中获取的第一手知识去启发工程技术,从而对如何理解大脑、重造大脑、保护大脑进行最为前沿的探索。
基础研究不仅费时费力、成本高昂,而且需要不间断长期投入,不论对于单个公司还是机构来说,长期承诺这样的无资金回报的持续投入,都是一个勇敢的决定。
科学探索是一场不问归途的冒险之旅,但纵观历史,每一次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的重大突破,都掀起了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原动力。
据“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