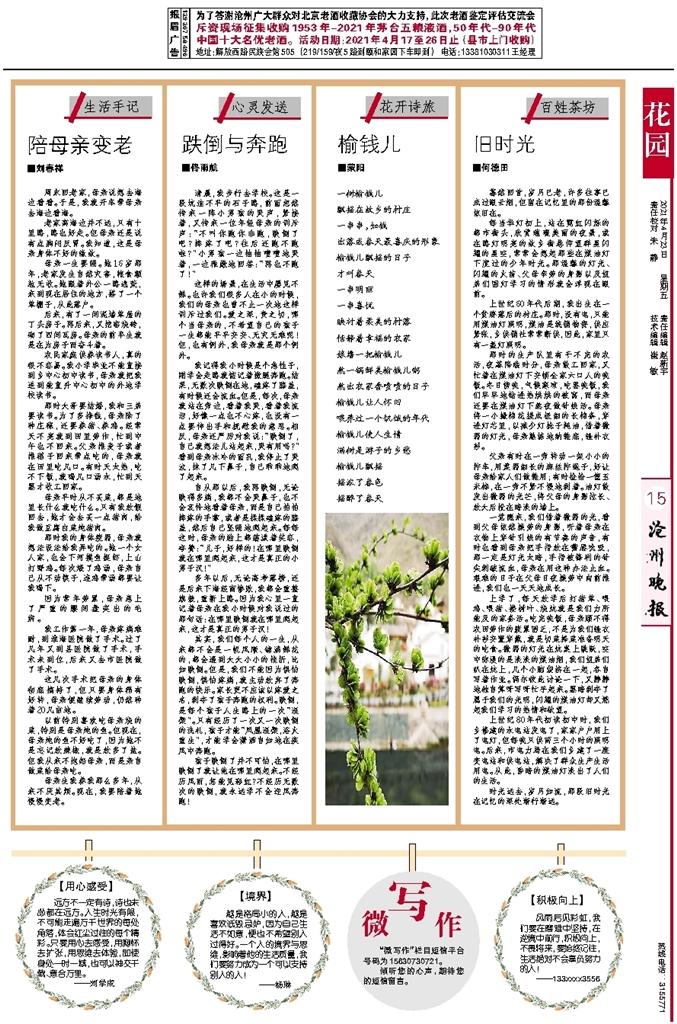蓦然回首,岁月已老,许多往事已成过眼云烟,但留在记忆里的那份温馨依旧在。
每当华灯初上,站在霓虹闪烁的都市街头,欣赏璀璨美丽的夜景,或在路灯明亮的故乡街巷仰望群星闪耀的星空,常常会想起那些在煤油灯下度过的少年时光。那温馨的灯光、闪耀的火苗、父母辛劳的身影以及姐弟们围灯学习的情形就会浮现在眼前。
上世纪60年代后期,我出生在一个贫瘠落后的村庄。那时,没有电,只能用煤油灯照明,煤油是统销物资,供应紧张,乡供销社常常断供,因此,家里只有一盏灯照明。
那时的生产队里有干不完的农活,夜幕降临时分,母亲散工回家,又忙着在煤油灯下安顿全家六口人的晚饭。冬日傍晚,气候寒凉,吃罢晚饭,我们早早地钻进热烘烘的被窝,而母亲还要在煤油灯下熬夜做针线活。母亲将一小撮棉花搓成极细的长棉条,穿进灯芯里,以减少灯捻子耗油,借着微弱的灯光,母亲熟练地纳鞋底,缝补衣衫。
父亲有时在一旁转动一架小小的拧车,用柔弱细长的麻丝拧绳子,好让母亲给家人们做鞋用;有时捡拾一筐玉米棒,在一旁不紧不慢地剥着。油灯散发出微弱的光芒,将父母的身影拉长、放大后投在暗淡的墙上。
一觉醒来,我们借着微弱的光,看到父母依然操劳的身影,听着母亲在衣物上穿针引线的有节奏的声音,有时也看到母亲把手指放在嘴唇吮吸,那一定是灯光太暗,手指被锋利的针尖刺破流血,母亲在用这种办法止血。艰难的日子在父母日夜操劳中向前推进,我们也一天天地成长。
上学了,每天放学后打猪草、喂鸡、喂猪、搂树叶、烧炕就是我们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吃完晚饭,母亲顾不得农田劳作的疲累困乏,不是为我们缝衣补衫安置穿戴,就是切菜择菜准备明天的吃食。微弱的灯光在炕桌上跳跃,空中弥漫的是淡淡的煤油烟,我们姐弟们趴在炕上,几个小脑袋挤在一起,各自写着作业。偶尔彼此讨论一下,又静静地独自算呀写呀忙乎起来。黑暗剥夺了属于我们的光明,闪耀的煤油灯却又燃起我们学习的热情和欲望。
上世纪80年代初读初中时,我们乡修建的水电站发电了,家家户户用上了电灯,但每晚只供两三个小时的照明电。后来,市电力局在我们乡建了一座变电站和供电站,解决了群众生产生活用电。从此,昏暗的煤油灯淡出了人们的生活。
时光远去,岁月如流,那段旧时光在记忆的深处渐行渐远。